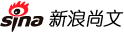切-格瓦拉之子:不想活在父亲的光环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01日 15:06 外滩画报
49岁的卡米洛·格瓦拉有着和父亲切·格瓦拉一模一样的额头和眼睛。只不过他不从事革命运动,他是一名摄影师。这是卡米洛·格瓦拉“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是1960年,在母亲的肚子里,和切·格瓦拉一同“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卡米洛·格瓦拉
卡米洛·格瓦拉北京798艺术区内的“古巴先锋艺术展”,一幅古巴艺术家伊斯梅尔·戈梅兹·佩拉塔绘制的切·格瓦拉肖像矗立在入口处。画中的切·格瓦拉头戴贝雷帽,留着大胡子,这是他早已深入人心的形象。一位中年人站立画前,和画中人有着一模一样的额头和眼睛,那就是切·格瓦拉的儿子,卡米洛·格瓦拉(Camilo Guevara)。
去年下半年,卡米洛·格瓦拉作为“古巴先锋艺术展”的特邀嘉宾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国行。
“第二次”中国行
适逢周六,798艺术区内的几个大型艺术展览同时开幕,园区内游人如织。一家艺术商店将印着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挂在临街的橱窗内,黑色的棉质T恤上镶嵌着鲜红的底色,切·格瓦拉的经典头像浮于红底之上,头像上方还印着“Guevara”的名字。
1960年,切·格瓦拉参加一次葬礼时,古巴摄影师阿尔韦托·科尔达为他拍摄了这张肖像照:紧咬牙关,眼望远方,红星贝雷帽下露出蓬乱的头发。这张照片被称为“世界上最有革命性最有战斗性的头像”,在切·格瓦拉去世四十多年后,这一经典头像仍在世界各地被反复翻印,深受艺术爱好者欢迎。一件普通的T恤衫,因为有了这个头像,价格便可以翻倍。
在从举办“古巴先锋艺术展”的程昕东国际艺术空间到餐厅的路上,卡米洛边走边拍,还不忘与同行的几个古巴艺术家说说笑笑。作为世人皆知的革命者的儿子,卡米洛没有继承父亲的遗志从政,而是成为了一名摄影师,同时他还是切·格瓦拉研究会的秘书长。
卡米洛手持一款纪念版的莱卡相机,上面印着红色的切·格瓦拉头像。他穿着白色衬衫,白色休闲裤,棕色的头发用黑皮筋扎着,身材高大,与人们熟知的切·格瓦拉相比较,卡米洛胖了不少。他将镜头对准了一件雕塑,人物是 “文革”时期典型的工人形象,紧握的拳头显得格外有力量。拍好照片,他得意地拿给记者看,他只拍了雕塑紧握的拳头,“这真有趣。”49岁的卡米洛不时地发出感慨。
“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对于第一次的中国之行,我没有任何印象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卡米洛·格瓦拉用西班牙语告诉策展人Raquel,说完哈哈大笑。
1960年,切·格瓦拉带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切·格瓦拉非常崇拜毛泽东,读过许多毛泽东的书。1965年,他曾再次访华。中国人的劳动热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美好的感情延续到他的子女中。
切·格瓦拉曾经结过两次婚,有五个子女。1959年,切·格瓦拉与第二任妻子、革命者阿莱达·马尔奇(Aleida March)结婚,卡米洛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卡米洛是切格瓦拉出生入死的战友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的名字。
在古巴,人们常说“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卡米洛对中国有天然的好感,但除了中国人勤劳工作和无私地支援过古巴之外,他对中国知之甚少。
我的父亲格瓦拉
2008年,“古巴先锋艺术展”的中方策展人程昕东来到古巴,在完成了展览等方面的协商之后,他向古巴的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见一下切·格瓦拉的后人。
“切·格瓦拉是很多人的精神领袖,世界各地的人到了古巴都会有类似的想法。”程昕东说。古巴国家美术馆馆长告诉他,切·格瓦拉的儿子也是一位摄影艺术家,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总会用镜头来记录,他的作品涉及种族主义等多种题材。程昕东喜出望外。
2010年初,程昕东在当地艺术家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古巴哈瓦那的一座三层别墅。别墅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椰树和各种灌木郁郁葱葱,这里便是卡米洛和母亲阿莱达·马尔奇一起生活的地方。
74岁的阿莱达·马尔奇留着棕色鬈发,有着圆润的脸庞和挺拔秀美的鼻子。1965年,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前往非洲继续开展共产革命运动。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俘虏,第二天便遭处决。有关与切·格瓦拉六年的婚姻生活,阿莱达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她把要说的一起都写进了书里。在出版回忆录《魂去来兮》(Evocation)时,她说自己对于回忆录并不热心,但四个孩子对父亲的了解不多,她对孩子们亏欠太多,所以才写下自己的回忆。
卡米洛指着一张沙滩上的照片对程昕东说:“这是我和父亲的合影。”照片上,切·格瓦拉身边的卡米洛还在襁褓中。他收藏着几张自己三岁之前的照片,既有和父亲的合影,也有父亲拍的儿时的自己,这便是卡米洛对于父亲的所有直观记忆了。
从小到大,母亲和父亲的朋友们总是告诉卡米洛很多有关父亲切·格瓦拉的事。切·格瓦拉在访问其他国家时,总是能得到很多礼物,却总是把它们送给穷人。有一次,阿莱达得到一台彩色电视机,却眼睁睁地看着切·格瓦拉把它送给了一个工人。还有一次,切·格瓦拉从阿尔及利亚带回家一大桶好酒,他让阿莱达送给附近的军队。阿莱达知道,喝酒对于切·格瓦拉而言,是难得的享受,便偷偷留下了五升。
虽然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但还是会寄来写着故事或者画着图画的明信片。卡米洛在幼儿园说脏话而挨了训,母亲阿莱达责怪父亲有说脏话的习惯。他当时在非洲,却写信要求卡米洛不能在学校说脏话。在信中,切·格瓦拉说:“你再说脏话,‘鳄鱼佩佩’(父亲编的童话中的动物)就会咬断我的腿的。”为了保护父亲,卡米洛从此不再说脏话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卡米洛说,每次回想起父亲离开古巴前的场景,母亲依然痛苦万分。在前往玻利维亚前,切·格瓦拉的行踪需要严格保密,他只能乔装打扮去看望自己的孩子。卡米洛依稀还记得,有一次母亲阿莱达指着一个看起来六十多岁的“乌拉圭人”,告诉四个孩子,那是他们父亲的朋友,名叫“Ramon”。“Ramon”和孩子们玩了一天,没人发现他就是切·格瓦拉。卡米洛的姐姐当时只有7岁,她在疯跑时撞到了头,身为医生的切·格瓦拉细心地照顾她。姐姐偷偷地对妈妈说:“那个‘Ramon’爱上我了。”
临行前,切·格瓦拉交给妻子一卷录音带,录的是朗诵的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在被处决之前,他托人转告妻子阿莱达,一定要改嫁,不要停止学习,照顾好四个孩子,让他们接受好的教育。
每次面对媒体,卡米洛总会被问到相同的问题“你对父亲有着怎样的印象”。他摇摇头说:“真的没什么印象了。儿时的模糊的记忆,和母亲讲述有关父亲的事情会混在一起,经常在梦中出现,让我分不清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真的记忆。”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切·格瓦拉遇害后的四十多年中,世界各地对于他的纪念从未停止。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阿根廷雕塑家安德烈斯·泽内利在两年多时间里,收到世界各地1.5万民众捐赠的各种铜制品,并用这些铜铸造了高4米、重3吨的切·格瓦拉像。在切格瓦拉被杀40周年之际,时任古巴领导人的卡斯特罗当天亲自撰写报纸文章,感谢这个“40年前的10月8号倒下的杰出斗士”;在玻利维亚,成千上万的人在切·格瓦拉被杀的村庄附近聚集,参加相关展览、讲话和音乐活动。
2004年,古巴前任领导人卡斯特罗下令在首都哈瓦那成立了切·格瓦拉研究中心,阿莱达·马尔奇担任研究中心的主席。卡米洛早年在苏联读书,回到古巴后曾经担任渔业部长,现在则担任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秘书长。
2010年10月,由导演特里斯坦·鲍尔导演的纪录片《切·格瓦拉》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放映。纪录片中展示了切·格瓦拉离开古巴时写给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封信,信的结尾写着:“为了永恒的胜利。”纪录片还包括切·格瓦拉幼年时期在阿根廷上格拉西亚的一段生活记录和他最后一次与父母相聚时的情形。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导演做了长达12年有关切·格瓦拉的研究。
“听到父亲的声音对我触动非常深,”卡米洛说,“以前很多有关我父亲的文艺作品往往只突出他的一个方面,要么是烘托他传奇的经历,要么把他塑造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这部纪录片应该是对他一生的总结。”
在“古巴先锋艺术展”现场,记者打算邀请卡米洛在一件有切·格瓦拉头像的作品前拍照。还未开口,卡米洛便大声对记者说“No”,摇着头走向展厅外。
中国之行前,卡米洛便和中方策展人程昕东立下“君子协定”——不能渲染他是切·格瓦拉的儿子。“他很独立,也很注意分寸。他不希望借用父亲的声誉来为自己谋求什么。”程昕东说。
在展览和访问的间隙,切·格瓦拉总爱随手拍照。卡米洛整理出六七十张切·格瓦拉的摄影作品,不是别人镜头中的英雄,而是切·格瓦拉眼中的世界。卡米洛告诉《外滩画报》记者,中国筹划切·格瓦拉的摄影作品展,是他此次来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
不是政治家,不是英雄,卡米洛展示给大家的是“摄影师”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有很多面,我想通过更多的对于他的准确的表述,来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他。”叼着古巴雪茄的卡米洛说。
B=《外滩画报》
C=卡米洛·格瓦拉(Camilo Guevara)
B:来中国之前,你对中国的了解多吗?
C:以前我以为在唐人街见到的就是中国的全部,后来渐渐发现并非如此。我对中国充满好奇,因为我想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样的;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不同层次的人如何实现自己的工作职能。当然,中国人改变现状的各种做法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B:在中国期间,你有哪些工作要完成?
C:主要是为古巴当代艺术展做宣传,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了解古巴的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50年前的9月28日,中国与古巴建交,我们的中国之行,也是为中国与古巴建交50周年做纪念;同时,我是“切·格瓦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秘书长),为了在中国举办名为“摄影师切·格瓦拉”的摄影作品展,我要和中国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会面,进行前期的商讨。
B:“摄影师切·格瓦拉”展具体行程是否已经敲定?
C:这个展览已经在世界很多国家举办,比如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南美洲的众多国家。我父亲曾经有一段时间从事摄影,拍摄并留下了一批作品,我希望大家知道父亲不仅仅是偶像式的人物,也是一名艺术家。我更希望把这个展览带到中国来,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日期,仍在商讨中。
B:你目前从事怎样的工作?
C:在古巴,切·格瓦拉研究会主要涉及学术研究和宣传这两个方面。学术研究部分主要是对切·格瓦拉的思想、作品以及和外界联系之后产生的印象进行研究,而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宣传推广方面,希望大家对切·格瓦拉的思想能有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
B:同时,你也是一名摄影师,在切·格瓦拉研究会和摄影之间,你如何分配时间?
C:在古巴的艺术家中,我可能是一个特例,因为我在切·格瓦拉研究会还有一份工作,需要在这两个工作中寻找一个平衡。要说一半一半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我就是为研究会来工作的,摄影是有可能的情况下才去拍摄。
B:你对摄影的兴趣与天赋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吗?
C:父亲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作为切·格瓦拉的儿子,我才有机会访问世界上很多地方,给我的摄影带来便利。但这并不能牵强地说我遗传了父亲在摄影方面的基因,我喜欢做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工作,我可以用摄影的方式去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
B:父亲去世时,你还不到5岁,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C:我对父亲基本上没什么印象,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一些斗争,特别是一些地下的斗争,他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是很快就离开了,我对他的印象只是梦中的印象,不知道对不对,也说不上模糊还是清晰。但我还是比其他人更了解切·格瓦拉,因为我妈妈和父亲的朋友们经常会告诉我一些有关父亲的事,我想还原他真实的样子,是切·格瓦拉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的样子。
切·格瓦拉有很多面,他不仅仅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军事家或者一个医生,他还是一个男人,是儿子,丈夫,父亲……他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他生活在现在,或许他会有不少新的创作和试验,抑或在另外一个国家,不遗余力地帮助那里的人们。
B:在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工作也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父亲?他的思想对你的日常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C:我主要是组织一些有关他思想的专题论坛,做有关他的纪录片,组织材料进行对外宣传,主要目的是让人们能够对切格瓦拉的思想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我母亲是研究中心的主任,是父亲的一个战友,同时也是一个游击队员,当时地下工作的战士,也是父亲最亲密的人,她现在的工作也就是要围绕思想学术问题进行研究。
除此之外,研究中心还会主持一些带有公益性质的计划,我还开设了一个摄影班,孩子们不但可以学习摄影的技术,还会知道怎样用这些技巧去为社区里的其他人服务。我想推广这些计划,重构古巴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在延续父亲的思想。
B:切·格瓦拉之子的身份给你带来什么?你怎么看待这个身份?
C:我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我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在西方国家,父亲也有崇拜者,但他们对父亲的宣传都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我生活在古巴,当地的每个人都尊敬他,家家户户都有一块纪念他的场地,这让我更有压力,一定要保存好有关他的记忆。有时候我会很不安,因为很多古巴人把对于我父亲的钦佩和赞美转达到我身上了。我不想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