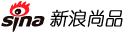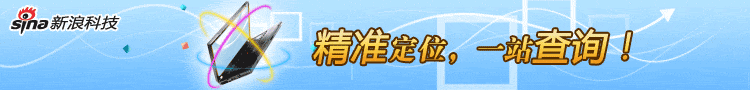为了这个岛屿而感动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13日 09:38 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
南岛文化圈指语言学上属于南岛语系的地域,包括了许多太平洋以及印度洋的岛屿。因为台湾原住民在这个文化圈中,语言的差异性最大,学术界一直有人认为,台湾就是整个南岛文化的发源地,古南岛民族未分化迁移前,就住在这个岛上。
 生活在台湾东南外海兰屿岛上的达悟族人,是台湾唯一的原住民海洋原乡
生活在台湾东南外海兰屿岛上的达悟族人,是台湾唯一的原住民海洋原乡南岛文化圈指语言学上属于南岛语系的地域,包括了许多太平洋以及印度洋的岛屿。因为台湾原住民在这个文化圈中,语言的差异性最大,按照语言学的理论,如果某一集中点的分歧最高,那么这个地点是起源地的可能性就最高,所以学术界一直有人认为,台湾就是整个南岛文化的发源地,古南岛民族未分化迁移前,就住在这个岛上。
向往之情缘起
来到台北,很难真正感受台湾是一个岛屿。台北的人口密度为9713人每平方公里,高过北京,至今是世界第二。建筑面貌上既有101那样的摩天高楼,也有日据时代的文化瓦平房。夹杂着大量的五六层无电梯的水泥公寓,外表铺着“二丁挂”(丁挂为日本人留下的模具单位,二丁挂是指宽度为6厘米,长度为其两倍的瓷砖),大多有20年以上的年头。阳台虽然有时候是唯一的光源,也被密密麻麻的植物完全遮挡,老台北人的家总是偏阴暗,难见天空。台北不可能不美丽,它的混血基因里最主要的两种缔造者——殖民者和逃亡者,都会将最理想的文化移植过来,制造它并无沧海相隔的错觉。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正坐在凝聚了这二者精华的紫藤庐里。这里从1921年开始为日本官宅,1950年转为国民党“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周德伟教授的家。周是哈耶克的门生,《自由宪章》的译者。1975年周赴美后此处转为茶馆。
整个台湾大学周边的街区都是这样的,很多日式院落还是校产,往往曾经是民国知识分子过海后的故居,又有一些被改造为咖啡茶馆和小店。我在台北的家就在这一带。世界每个都市都有这种文化盆地,深陷进历史的阴翳,古意盎然,情调高雅,人精会聚,房价冲天,住久了就有在巴黎左岸六区家里同样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温州街有一个书店叫“台湾e店”,闽南语意为“台湾的店”,里面放满了关于台湾本岛、日据时代的历史,以及原住民历史文化的数据。后来才听说这是台北最“绿”的书店。所幸我对颜色毫无成见,才借由这些资料,发现自己其实身处在一个“野”气盎然的南岛之上。
考古界前辈,做过“中研院副院长”的张光直先生笃定地说:“台湾这个宝岛上所有大家都知道的很多有学术价值的材料中,如果让我说哪一种材料是最有价值的,我的回答是,台湾的原住民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上面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南岛文化圈指语言学上属于南岛语系的地域,包括了许多太平洋以及印度洋的岛屿:北起台湾,南到新西兰;东发复活岛,西至马达加斯加。因为台湾原住民在这个文化圈中,语言的差异性最大,按照语言学的理论,如果某一集中点的分歧最高,那么这个地点是起源地的可能性就最高。所以学术界一直有人认为,台湾就是整个南岛文化的发源地,古南岛民族未分化迁移之前,就住在这个岛上。
台湾现在承认的原住民包括14个民族:阿美族、排湾族、泰雅族、布农族、鲁凯族、卑南族、邹族、赛夏族、达峿族、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赛德克族。他们中只有邵族属于过去的“化蕃”,也就是汉化程度更深的民族,其余都属于日本人称呼的“生番”。而日据时代的“熟番”,也就是平埔族,早已完全和汉人同化了。
对于人类学,我这个艺术史专业的是个外行,但是向往之情和张爱玲的理由相似,因为总向往更加荒古的东西,而“人类学比考古学还古”。更巧的是,张爱玲在这件更古的事上,谈得最多的是一个改编成电影的真实故事《叛舰喋血记》,讲的就是一艘英国军舰流落南岛小岛屿发生的事实。她为此还钻研了南岛民族中常有的关于“小矮人”或“小黑人”的传说,并在《谈看书》中专文详述。后来,跟建筑师谢英俊和他爱人郑空空相识,他们是常年住在部落里,为原住民建筑家园的人。在他们指引下,我终于有机会从书本里出来,去拜访台湾中部的邵族和南部的排湾族部落。
画眉鸟还没睡醒
2011年,伊达邵的祖灵祭在9月17日进行尾祭。我们早了两天,15日就赶到了日月潭边东南角的伊达邵部落。落脚的酒店是全桧木建造的哲园。桧木产自此间山林,是日本皇宫的主要建材。伊达邵码头边的坡地上发展出一个拥挤的观光小区,共有8家大小不一的酒店,一条叫做日月街的主要商业街从码头爬伸到环湖主路。有一个邵族文化活动中心,显然是一个失败的政府项目,成了台湾人说的“蚊子馆”。很难看出这里就是邵族的聚居地:德化社。
我们的目的地要从小镇向上,穿过环湖公路,左手有木刻的邵族大偶人,写着“伊达邵欢迎你”。再向上走50米,左手有一块台地。
邵,据传是从台南平原或阿里山北上来到这里的。传说中他们追逐一头白鹿,发现此水草丰美之地,就开始在潭中心的一个独立小岛:拉鲁岛上定居。后面的故事是一个avatar的原型:族人以岛上一棵30人方能环抱的茄苳树为保护神,年年祭祀,而得兴旺发达。最终,清朝政府派人来把茄苳神木锯断,还盖上了铜锣,使它不得再生新枝叶。
后来日本人为了发展台湾轻工业而兴建日月潭发电站,邵族的多处家园被水淹没,几个社合并迁居于今天的德化社(日人的命名)。如今他们由水沙连最强大的部落,变成了人数最少的一个原住民族,仅存281人,大多数居住于德化社。这么少的人数融在日月潭观光产业的底层职业中,却让人难以置信地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祖灵信仰和祭祀习俗。比如他们大多数人家门口的晒谷场,也就是祭祀用地,在寸土寸金的日月潭边被商人或政府强征或出售。他们却坚持,即使在马路上,也要完成每年的祭祀仪式,用两根竹竿拦起来,与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争夺出一段属于族人的神圣空间。
我们的车从主路进入小区,迎门放着一台被涂上颜色、画上邵族图案的中型吊车。后来才知道,这块环湖公路上的台地,亦是政府和地产商均欲染指的地方。“9·21”大地震后,山下族人的房屋80%倒塌,相关部门不同意邵族在此台地重建家园。但是在政策拖延之间,邵族人在谢英俊建筑师的带领下,3个月修完了所有的房屋。
建筑族人家屋的速度快,来自两个重要因素。首先,谢英俊为他们专门设计了搭建非常迅捷,却又防风抗震的房屋结构,外部全部使用族人熟悉的当地材料,比如竹子。谢英俊多次向我解释原住民的某种生活哲学:他们都是活在当下,活在现场的人,每天的天象物候,人的状态都在变化,不可以提前太多去计划。而且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用人的双手能够着的材料,用本地山水现场里的好东西。其次,在邵族的历史上,建任何一个成员的住宅,都是全族人的事,全体族人按男女老幼分工,建哪家就由哪家主人负责晚上的酒肉。
这种以换工方式集体劳动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建设效率,促进了族人的公心。也节约了去外面请包工队的金钱。所以,是特殊的部落集体生活的哲学,帮助邵族人“占领”了这块本来就是他们家园的土地。在部落门口,那个当初大家齐心协力建家园使用的吊车,被做成一个装置来以兹纪念。
再向内走一段,右手边出现一块奇怪的牌子,上面写着:“公用捕蛇器,用毕请归还。”旁边放置着一根带钩子的长竿和一个铁笼子。这是部落用来捕捉入侵住宅的蛇类的,有的蛇会盘踞梁上或床下久久不去,其中包括百步蛇、眼镜蛇等剧毒蛇。族人捕到蛇后一定会将它放生,百步蛇还是他们崇拜的灵物。邵族和蛇之间玩着这个无休止的游戏。
继续向里,还有人家的外墙上画着猫头鹰,据说也是他们崇拜的当地动物。我们一入夜就听到了它的鸣叫声。继续深入,会看到一块长方形空地,空地北边是头目的家。这应该就是晒谷场和祭祀用地了。空地西侧有一座茅草搭起来的小屋。屋门口又有一个字牌:“祖灵屋,外人勿入。”我们走到部落最深处,部落会议室的旁边有3间大屋,那就是谢英俊和空空在邵族安的家。
黄昏降临,聚落的面貌开始转变,现实的轮廓模糊了,随着家家户户门口的篝火点燃,我们的身旁变得更充实和拥挤了。篝火是由后山砍来的樟木烧的,木段还是湿活的,树皮上生长着油绿的苔藓和蕨类。台湾盛产樟木,是世界樟脑油的主要出口地。再扣上几只刚剥完的文旦皮(一种小柚子),火焰立刻有了特殊的芳香。
谢英俊如同肉铺掌柜一般拿出一块洗干净的猪后臀肉,大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厚度在三四厘米间。我急忙站起来想要帮他打理。他却摆摆手,直接在火上架起一张并非烤肉专用的铁丝网,把这块东西甩了上去。撒了些盐,就用一个大锅盖盖住。每面来个15分钟,这东西变得毫无腥膻,肉汁微甜,而且天然地带着樟木和柚子熏肉的香味。
后来,我们又在这火上烤了茭白和蘑菇。就着这一堆火,一点盐,一锅白米饭,吃了顿此生或许不可再有的晚餐,也是原住民典型的晚餐。饭后,所有荤菜的剩余,骨头肉渣,都只需用力扔向屋前一块长满草的斜坡。不一会儿,你就会听到草丛里窸窸窣窣,不知是什么动物开始发挥自动垃圾处理的功能。第二天那草地一片清新,毫无曾经荤腥过身的气息,真不能想象有多少动物在部落里和族人共同生活呢。
大约20点左右,空地祖灵屋那边传来了歌声。谢英俊和空空默默地进屋换了一身行头,披上了一件红色的手工致花背心,向着祖灵屋的方向走去。
祖灵屋旁的长方形空地上,已经有五六个人手拉着手,静静地站成一圈,随着头目之子阿贵的领唱而齐声诵唱。其中声音格外嘹亮自信的是几位五六十岁的阿妈。她们被称为“先生妈”,是族里的女祭司,负责与亡灵沟通。祭祖的歌词在族人间口耳相传,不得在非祭时间随意吟唱,因为那会让祖先误会,从而发怒降祸于唱歌的人。所以有些歌词的含义,甚至连先生妈和头目也不清楚具体含义。随着一曲曲祖灵祭歌的声音,逝去的所有祖先们将会回到这间祖灵屋里,围绕着屋里为他们烧起的火炉,和我们刚才一样,烤肉、烤菜,喝酒、唱歌。同时,在空地的一角已经点起了明火,架起了一头四脚撑开的大猪。
阿贵的父亲,也就是邵族的头目,和族中几大家族的老人,都坐在头目家的屋廊下。老人在一身民族服装之上,戴着一顶方顶男式礼帽,材质是灰色法兰绒的。邵族人的体形比我们之前见到的排湾族人要瘦削一些,老人坐在那里,深目高鼻,如同当年的人类学家所写,“毫无汉人的斜眼角”。他一动不动,而只要我接触到他的目光,就会情不自禁地改换一下自己身体的姿态,仿佛相对于他,自己总有些什么地方没有稳住。
舞蹈的步伐相当简单,我相信在这样长时间的吟唱和踩着单一节奏移动摇晃中,人会进入一种出神状态。这样缓慢的祭祖歌和舞蹈,大约要进行两个钟头左右。这个过程中,圆圈是完全流动的,人随时可以离开或加入。进部落的主路上,不断有摩托车、汽车声响起,那是不住在这里的部落人从四面八方回到祖灵屋前来参加歌舞。除了主祭家人,先生妈以及一些住在这里的老者之外,其他人都穿着他们日常的衣服,高跟鞋、牛仔裤、校服、T恤……小孩子一旦加入圆圈,旁边的大人不论身高多少,都会谦卑地弯下身子来维持和他们牵着手的状态。牵手非常重要,根据我的舞蹈经验,那是让身体能量交换循环,成几何倍增长的方式。
在慢歌阶段过去后,大家要由主祭的小伙子领着排成一条长龙队,维持着牵手的状态,进入祖灵屋巡回一圈之后出来,沿着部落主路,到部落的48户住宅的门前去绕一圈。领队的人拿着木棍敲打地面,他们自动分成两个声部,前声部问,后声部答,大意是新年要扫除邪恶污浊的东西。队伍一定要真正踏遍部落的土地,再回到头目家门口的广场。
慢舞自此结束,他们再站成一圈,阿贵重新开唱,从此刻起,节奏在默契中被大家的嗓音慢慢带快,越来越快,小朋友会被妈妈带着离开圈子,然后年长的人,先生妈们也退出了。圈子开始飞旋,转动的人数越来越少,剩下的通常是中年妇女和年轻男人。其中有一位身材妖娆、长发飘飞的女人,大约45岁的年纪,一直光着脚,跟小伙子们一起旋转。
人群只剩下一个微小而强大的“原子核”在高速转动,四个人,三个人,两个人,像摔跤一样扯着对方转圈……一个人终于甩开手臂时,那个坚持到最后的就算是勇士。今天的整个歌舞祭祀就结束了。
那只火上的大猪已经被削了好几次肉,被切好分匀在一个个方便纸盘里。剩下骨架在烧烤。领队的小伙子拿起一个扩音电喇叭,用台普朗读:“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后面他会宣布所有现场的赞助人,大多数都是赞助各类酒水,或是几千台币的现金。比如:“来自对岸,北京的张女士赞助,台湾啤酒两箱!”于是我和我的啤酒就得到了全场人鼓掌欢呼。
只有一位赞助者有点尴尬。“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参加‘立法委员会’原住民代表的竞选人,×××先生赞助大会台币3000元。现在,我们欢迎他讲话。”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开始在饥渴难耐的族人和一顿烧烤啤酒大餐之间,插进他的政治理念。据说每个原住民的祭祀节日,都会有竞选原民代表的政客来拜票。而邵族人早就习惯了,政客来了要讲话,就让他讲话;学者来了要考古,就新做几件给他收藏……抱着一套自己的想象模式来的人,都会得到这样的款待。政客讲完,大家一拥而上,每人都分得一小碗烤肉,肉旁摆放了至少三四种辣味调料,可见他们的重口味。
17日的尾祭开始前,我们就必须离开了。本来是很遗憾,可是细细想来,以我的酒量和精力,也不敢参加。那意味着从头一天傍晚持续到第二天下午,要到每家门前去歌唱跳舞,然后享受那家人特意为所有人准备食物酒水。据说一结束,就看见部落里一片零乱:鞋子丢在路上,头花到处都是,酒瓶捡一个星期还捡不完。
不过,我倒是有时间仔细请教了关于祖灵的事情。原来邵族人和许多其他原住民部落一样。在人逝世后会让他保留坐姿,放进一段空心木头或一个罐子里,直接将这个装置葬入家里大厅的地下。他们深深地相信灵魂不灭,但绝不认为肉体可以复活。祖先的灵魂不要离开自己的家,要仍然和家人每天生活在一起,这样家族的力量才不会被削弱。后来日本的“理蕃政策”中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不卫生行径,规定他们必须将族人葬在村边的某处坟地。
邵族人家如今还保佑一个祖灵篮,篮子里放着所有能收集到的逝去的先人穿过的衣服。祖灵篮的神圣是日常生活的神圣,所以它不会被专门供奉。通常是挂在厨房的某个地方,梁上,灶旁,窗边……
祖灵不尽存在于家里、部落中,也存在于族人生活的所有地方。他们听到山风,会认为那是看不见的勇士在呼啸;看见枝动,会想到有一个化为灵魂的勇士正经过。
祖先的规矩在从前是很严厉的,有许多现象被视为不祥,如果看见,就要立刻回家,因为只有家,有祖灵护佑的地方,才可以让你免灾。据说一个排湾族人要去20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在路上打了个喷嚏,就断然从走了15公里的地方掉头回家了。因为喷嚏对他们是十分不祥的兆头。而邵族人也有看见画眉鸟从左边飞来,就无论如何要回家的规定,至今仍然被族人虔诚遵守。阿贵告诉我们,如果你今天真的有重大的事情,要谈生意、相亲呀,就请天亮前起床出门赶路,那时候画眉鸟还没睡醒。
他眼中的今天下午
5月中旬,我们又从南回公路向北,进入太麻里地区,先去金峰乡医疗所拜访一位排湾族医生。走到台东县金仑社卫生所门口,我发现了两个入口,侧面一个缓坡,正面一条陡峭的水泥台阶。应声出来迎接我们的高医师指着正面的台阶说:“那是政府要求原住民恢复传统,说金仑社的每一户都要朝着日出的地方开门,所以我们就增加一个高高的门供起来,一看就不是给人走的。”
高医师50岁上下的年纪,高大臃肿,因为饮酒过度导致痛风,使他走路很慢,有一种雍容的拖曳。他也跟阿贵父亲一样,常年戴一顶麂皮做的牛仔帽。一摘下来,一缕灰白的头发像老猎犬一样扑出来。高医师的办公室在三楼,窗户正对着太平洋,只有台铁火车经过的时候给海洋和陆地划出一条临时的界限。桌上留着一本翻开的日本人做的台湾原住民摄影集,书柜里放满了关于原住民和南岛文化研究的各类资料。
日据时代,日本人限制台湾人接受高等教育。对汉人开放的公学校中有两种科目最受台湾人欢迎:医科和师范科。所以当时台湾社会的众多精英都从事这两个职业,当时闽南语中也只把老师和医生称为“先生”。这个习俗对台湾人的影响,在高医师这辈人中仍然能看到。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也通日文,是金峰向正兴村的排湾族大头目。排湾族是保留贵族世袭制度的民族,头目的儿子通常会从事比较尊贵的职业。
吃晚饭的时候,高医师也带来了他的儿子,一个染了金发的精瘦小伙子。席间小高幸福地告诉我们,他的职业理想是做个鸡尾酒调酒师,过阵子就要去台北学习了。他的理想是,把排湾族人的小米酒带到世界上去。2010年屏东的吴宝春以酒酿桂圆、黑糖、荔枝等西方人完全陌生的口味加入面包而一举获得法国面包大赛头等奖,其中就使用了原住民酿的小米酒。由于原住民的饮食哲学从来都是取自天然,有着天然的优势。
饭后我们一路去高医师家参观一个刚刚搭建起来的“订婚台”。高医师家有着头目家的特殊装饰:订婚台由4根竹竿,夹两层九穹木桩垒成,总高度约一根电线杆。上半部是一根一人高的竹竿,竿头保留着茂盛枯黄的枝叶如旗帜。在枝叶下用红丝带系上木枪、木刀和鹿角,再往下一点系着一朵百合花。高医师特意用手电为我们照亮九穹木桩中部的一个位置:一个完整的九穹木树杈被顺势雕刻成女性阴部的样子,在树杈的分叉处放置了棕榈树的纤维以示毛发;对着分叉口,反置着一个男性器官的木雕,也是用九穹木雕的,刀法挫滞,十分写实。
九穹木的质料坚硬,难于砍伐,是台湾人做砧板的好材料。之所以要用它来做,一来是为了考验男人的体能和决心,二来是象征着结合的坚实。砍伐九穹木要求新郎召集全村的青壮年来帮忙。这件事情并不复杂,因为排湾族和台湾许多原住民部落一样,都有青年会这个组织。青年会具有实体上的物质空间,往往是一间大屋子,里面可以睡下村里所有的男人,未婚男青年会在这里居住到结婚,而已婚男人在成亲后一段时间内也要先住这里,夜里与妻子相会,直到生育。其他男人则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到这里来混单身,譬如和老婆吵架啦、家里来亲戚啦等等。
订婚台最高处系的鹿角和木刀枪,都象征着男性的勇武;下面系的百合花,一方面象征着女性的纯洁美丽,也是原住民长期以来信仰基督教后引入的圣母象征。
女性器官的发想来自男孩子们的树杈情人。爬树几乎是排湾男孩子一会走路就会做的事情,树上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了:除了芒果,龙眼,伯劳鸟窝,百步蛇……还有比它们都可口和危险的性幻想。青年会的男孩子们一起在树林里干活的时候,都会认一个树杈做他的爱人,当然是因为他喜欢骑在上面做任何白日梦。而其他的男孩子也就会尊重他的选择,不再去那个树杈上作乱。直到他可以做订婚台了,那个树杈就真的会变成他的爱人的象征。
至于代表新郎的那个器官,一定是这个准备结婚的男孩子一手雕刻出来的。一定要做的尺寸比他的“树杈”小一些。原住民的雌雄尺度概念认为,男人称大的时刻应该是在狩猎场上。在婚姻家庭中,雌性和母性一定是更“大”的。这种大是有生理基础的,想想这世界上,哪有一根雄宽得过一杈雌的?他们明白,这个时候,雄性需要被接纳,被包容。
订婚台从订婚之日搭起,可不是在结婚之日拆除,一直要到女方怀孕之日。高医师作为头目和医师,有一个“missionimpassible”,就是密切观察新婚夫妇,如果过了一年还没动静,他就会找男人谈话,如果这个男人自己有身心问题,他必须把他带到他的订婚台前,给他一通教训。
“你都跟他们说什么?”
“请求祖灵眷顾这个孩子。”高医师眯眼笑着,“然后让他来诊所,我给他讲讲A片不会教的事,包括什么时候不能喝酒等等细节。实在不行我还会给他开点药。”
可是,什么时候能不喝酒呢?在19世纪,就有西方人记载:“他们像印第安人一样真正喜欢烈酒,而为了换取酒喝,他们可以割舍任何东西。”还有人发现原住民部落的小孩子,四五岁就可能处于酩酊大醉的状态。我已经在很多户门口看到了被撞得奇形怪状却还在被使用的车。在每一户人家的屋前都有一个简单的烤肉炉,炉边放着成堆的台湾啤酒或米酒的酒瓶。Barbecue,对于原住民是日常生活,并不是周末的中产阶级仪式。没有点火烤肉喝酒的一天,是非常不吉祥的一天。
只不过从前,酒是小米酿的,肉是山上打来的。
丰饶的猎场
几乎每个男人都酗酒,我们的车驶过重建的玛家农场。16点多,几个戴斗笠的女人在农场边的一小块地上烧荒。几个男人坐在一家小吃店的门口,已经喝光了几箱啤酒。问那些忙碌的妇女:你男人去哪里了?她会告诉你:“我男人也很忙呀,忙着在树下喝啤酒,骂政府。”
下山定居,原住民的雄性任务基本被撤销,映入我眼帘的是空虚不安的眼神,肥胖迟缓的身姿。青年会在2010年才正式恢复,训练的时间缩短到暑假两个星期,而作为训练主要项目的狩猎,则更加是个问题。原住民以为养殖是个悖论:养了动物又要杀掉它,他们无法做到。所以只在应该狩猎的季节猎取合适的数量,而且它们的灵魂得到了祖先的认可和保佑。史温侯(RobertSwinhoe)在1859年的游记里曾记载,清政府为了消灭凶狠的生番,曾经从大陆引进老虎放入台湾的深山。但是由于蕃人狩猎技巧太高,最终被消灭的显然不是他们。
如今早已无法用猎物来作为肉食的来源,但是仍然有几种特殊的日子需要狩猎:祭祀祖灵的日子;有人去世的日子,丧家必须马上做“除丧狩猎”,只有这样才能让亡灵回到祖先的“猎场”。高医师告诉我们,身后就是大武山自然保护区,政府为了修建这个保护区,把原住民从山上赶到平地,而且设立了许多破坏他们基本生存原则的条例。他自己画了一张图,标明了在山中的原始的部落28个社,如何被迁下来合并为嘉兰、正兴、新兴、宾茂和历坵五个村。
其实原住民的狩猎习俗由来已久,视山野为生养他们的母亲,十分重视保育环境和动植物,“因为我们就是狼,就是鸟,就是蛇,我们和它们一样”。自然从来没有因为原住民的存在而受到过伤害,修水坝,建高楼都不是原住民的生活。
2010年,日本的山猪国际会议在台湾召开,这是一个日本猎人和原住民部落专门就人和野猪的关系而组织的年度会议。野猪从来是南岛语系的原住民部落主要捕猎对象。日本人认为,是野猪“把他们带到一个未知的领域,让他们了解到另一个物种的价值和意义”。2009年曾经邀请排湾族猎人去日本冲绳县西表岛参会,西表岛有90%的面积是原始森林,同样面临着国家建立保护区和维护原住民狩猎传统的问题。大社部落的排湾族人Sakuliu发言说:“狩猎这件事情,为了灵魂的荣耀远超过吃肉。一个猎人的伟大,不是打到多少猎物,而是他的猎场有多少猎物……丰饶的猎场,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猎人的使命,是维护猎场的丰饶。在他们的祖灵信仰中,每个族人的灵魂最终都会回到祖先的猎场,那就是原住民的天堂。所以他们各自都有维护生态的一套:比如捕捉数量以族人够吃为限,绝不多捕;在陷阱中控制好踏板重量,这样体重轻或年幼的动物就不会掉下去;一到3月,此地溪流中产毛蟹和秃头鲨,他们就吃这些水产,4到6月,动物数量增多,就吃兽肉;秋冬天台风多,动物少了,他们就减少肉食……
现在的问题是,台湾当局只允许他们每年申请两次狩猎机会。一次申请要至少半个月才能批准下来。许多基本的捕猎对象被列为保护对象,如山猪,山羌,山羊,鹿,熊……正兴村保我目里部落头目勒马力子说:“飞鼠根本不能算猎物,不能向祖先、头目和长老报战功,这样我们的祭祀里就无法唱出报战功的歌。”战功歌是排湾族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吟唱篇章,而如果没有猎到相应的猎物,是不可以随便唱的。而丧家狩猎是家里一旦发生丧事要立刻做的事情,这样祖灵才会接受这个回来的子孙,才能将逝者下葬。生死非人力可以操控,除丧狩猎也很难在政府繁琐的申请规则中被批准。
保护荒野,是否要将居住在荒野上的原住民都驱逐?排湾族碰到的这个问题,比邵族碰到的强征土地用做商业要更隐蔽。从1862年开始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开创了广为传播的“国家公园”模式和永难平复的保护区原住民抗议活动。水泥森林的建造者和汽油的使用者,打着环境保护的名义驱逐与山海共生的同类,用自己的生活方式谋杀他们,从而欺骗自然,使这些地方成为强势人群炫耀的休闲之地。而真正“致命”的,从这个词的原意来说,还不是以上这些话题。每一个原住民部落在山上都有自己的“猎场”,猎场边界是相互尊重,不得逾越的,是祖先所立。而现在部落聚居地被拆迁打乱,政府就近规定的狩猎区不仅常常不是原部落的猎场,甚至是其他部落的地盘。每位部落头目在谈起这个问题时,都会十分严峻地告诉你:“这种事情要是放在从前,一定会‘出草’的。”
Headhunting
猎头是全球许多原住民部落的习俗,在台湾归属的太平洋南岛文化中亦普遍存在,台湾本岛除了位于兰屿离岛的达悟族之外的十三族,在日本人的“理蕃”政策实施之前,均保有这个传统。去猎人头又叫做“出草”,因为原住民都是从隐蔽的野草中突然现身来袭击对象。怀特(FrancisWilliamWhite)在1870年写道:“生番认为,只要能得到一个客家人的头壳,付出两三天不进食来监视的代价是很值得的。”
猎头的本质动机是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常常是针对周围的其他部落和入侵者,以壮大本部落的力量。部落哲学的重要根基之一是,部落的力量不仅是活人的力量,它的源泉是逝去的祖先灵魂的力量。他们认为获取了人头就获取了此人灵魂的力量,他的灵魂也加入了本部落的灵魂大军,增强了祖灵的部队;而本族人若丧身在外,他们也要力争夺回尸体,否则就会很沮丧地看到同族的灵魂皈依了敌人的祖灵。“出草”亦可被视为一种灵魂争夺战,从这点上来看,绝对是今天的猎头公司的祖宗。
由灵魂崇拜而为猎头发展出神圣的宗教意义,在重大灾难发生需要祈福或进行其他重大仪式的时候,也会先出草祭祀祖先。一个部落男孩子只有割下了第一个人头,才算做成年人,才有结婚的可能,所以成人礼和婚礼也是以出草为前奏的。婚礼时整个村子都围聚在新娘父亲的门口,把战场上赢得的头盖骨带上前来,呈献给新娘。那头盖骨让新郎获得结婚权。新娘用它将酒与脑混合成一份饮料,然后将它传给所有在场的人作为爱杯,由头目开始,到新郎为止。部落里的男人获得的人头越多,他的阶级和地位就越高。日据时代之前,部落里的人头是一定要在家中或部落集中的地点展示的。
苏格兰牧师甘为霖(WilliamCamp-bell)于1847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串头壳,绑在酋长屋子的末端。几乎都是开裂的,不少还有一些人肉黏附,似乎一两个月前才从身体上割下。其他多数的屋子也都如此装饰。在一个小草屋那里,我数了数,共有39个头壳,另一家有32个,第三家有21个,等等。有人告诉我,那些是他们部落间打仗胜利,还有成功袭击高山西边居民的战利品……从其中一个椽木上垂悬的厚厚一团长发,无疑的,是由被谋杀的熟番与汉人的辫子所组成。他们的头壳正在外面漂白……”
清代台湾府的首任知府蒋毓英在《台湾府志》中也记载过:“好杀人取头而去,漆其骨,贮与家,多者称雄。”排湾族的五年祭中,勇士们要用竹竿猛刺被抛在空中的头颅,最后刺中的被视为勇士,人们就都去他家跳舞。后来已经改为刺藤球。
1905年,日本开始实施“理蕃政策”,“理蕃”准许的最后一次出草发生在1920年11月20日,是日本人主持的。起因是这个地区泰雅族色拉冒蕃佳阳社族人发起抗日活动,日本人鼓动亲日的雾社蕃巴兰社壮丁124名,由其头目率领,剿灭了抗日活动,获取25颗“凶蕃”首级。仪式在日本治理机构雾社分室前的操场进行,完全按照部落习俗进行,日本人和得胜部落的人都参加。最后由分室主人宣布这是台湾历史上最后一次出草,今后不论日本人、本岛人,还是蕃人,违法杀人者,彻查处死,绝不能再出草杀人了。这次仪式还留下了日本人、蕃人和所获首级的合影。
事实上的最后出草,却不幸发生在11年之后的同一地区,同样由日本人支使。
1930年,雾社地区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发动赛德克族6个部落共1236人,其中青壮年314人,趁日人在雾社公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之际,发动大出草,血祭祖灵。结果共杀死了134名日本人,重伤26人,杀伤215人。事后,日军的报复使六部落仅存514人,被关押在雾社的看守所。1931年4月25日夜,和这些部落有宿仇的道泽群社潜入看守所,杀死和自杀的人216名,出草人所获头颅101颗,并且向日人邀功,有照存留。由于大量人进入看守所杀戮,而看守人员和日籍人员无人有毫发伤亡,后世学者大多认为这真正的最后出草,仍是日本人暗中安排的。
落山风
还是这个5月,我们从高雄沿着西海岸的屏鹅公路向南。前半段看到的是台湾西海岸的沙滩,因为台湾海峡大多是大陆棚构成,平均深度只有50米,而且这段路上溪口多,山上的河流携带大量沙石入海,所以海峡这边的水看上去比较浑浊。从枫港开始,溪口消失了,水质清澈,适合珊瑚生长,海岸景色转为恒春半岛的珊瑚礁海岸,台湾有300多种造礁珊瑚,全世界也只有500多种。而珊瑚礁是海中的绿洲,生物多样性是最高的。一路上,我们都能看到在珊瑚礁中讨海的人。然后从温泉路向东,离开海岸向着中央山脉进发。温泉路是台湾南部一个泡汤的好地方,从二重溪到四重溪,两边遍布温泉酒店,一直延伸到石门古战场。
台湾的陆地面积仅占地球的万分之二点五,物种数量却占全球的2.5%,海域生物物种更是全球的10%。在这山海之间,有最原始的南岛文化,这些民族在用和我们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人类短暂的宇宙生命。在由海入山的车上,我发现“多样性”这三个字,才是这里最可贵之处,不禁对谢英俊夫妇说:“千万别让这么美好的东西被任何一种‘岛内共识’给同化了,对我来说,台湾是一个野胜于文的地方。”
此时,山沟里开满了紫红的杜鹃花和九重葛。这里是中央山脉的尾棱,海拔最高仅1000米左右,所以植被大多数是我这个南方人熟悉的:野千日红、蛇莓、节节草、满天星……森林覆盖率相当高,树种却比较单一,最多的是相思木,除此之外最美的是正在开花的大头茶。据说是王永庆的造纸业买下了附近的大片山林地,都改种造纸的原材料相思木,而相思木与许多树种相克,以致生态单一化,动物都相继离开,特别是各种以不同植物为食的鸟类。所以这一带的森林一片死寂,是真正的“鸦雀”无声。
从石门开始,这条路开始叫做石门路,一直引导我们走向牡丹乡的中心。温泉酒店消失了,人烟越发稀少,大山越发沉静。沿路没有任何商家、店铺和餐厅。石门村,当年这里的排湾族原住民,被外来者公认为最野蛮凶残的族人。1874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第一次海外出兵,就发生在此处。当时牡丹社、高士佛社,以及女仍社的原住民殊死抗日,最终不敌。这次出兵的原因复杂,本来是这里的原住民杀死了一些流落岛上的琉球渔民,应该由清廷来解决。日本主战派以其中有4个日本渔民为借口。向清廷请战,时清朝台湾府官员毛熙回答日使:“生番系我化外之民。”意为清廷不想管这件事,给日本人创造了出兵的好理由。
妄图长期驻兵的日本人最终虽因不敌湿热气候而求和,却首次尝到了台湾岛的真滋味。而清廷因为日本人的举动,也开始大大加强对台湾南部和“蕃人”的治理。
14点钟左右,我们在牡丹国小的路边,走进一家排湾族开的小吃店,这样的小吃店在整个牡丹乡有两个,上面那个已经关门了。老板在店门口有一个卤味窗口,这里是餐厅肉食的唯一来源,由猪和鹅的各种部件组成。主食每人一大碗油渣板条(一种类似云南宽米粉的带汤米制品)。山上的新鲜蔬菜显然不足,我们想要一份烫青菜,老板说店里已经没有菜了。他的女儿上三年级,今天下午没有课,在店里帮我们端菜。
饭后我们继续开车,目的地是牡丹乡里位于最深山中的一个部落:高士佛部落。要从石门路向南,走一条在地图上没有名字的窄小山路。随着入山越深,开车的谢英俊建筑师告诉我们,这个部落在2009年发生的“八八水灾”中完全被摧毁,现在政府在临近处为他们选择了一块重建的新地址,但是问题很大,主要是生活物资供应困难。从日据时代开始,高士佛部落住地被视为军事重地,因为它位于中央山脉尾棱港仔山的最高点,东望太平洋,西看台湾海峡,还直接俯瞰着恒春平原。但是这里生存条件恶劣,部落中的妇女每日下山背水才能够供给族人和日本占领者。春季和冬季,还会刮起落山风:由于此处中央山脉呈现向南缓降的趋势,从太平洋来的东北季风非常容易翻越山脊,在背风坡形成湍流。风势之大,至今可以影响南回铁路的火车和恒春机场的飞机运行。
高士佛新址还是一片刚刚整理过地基的工地。唯有一座小丘上的日本神庙得以保留。我们登上小丘,神庙只剩下一根石柱的基底,被开着小白花的酢浆草和三叶草包围。向东方和西方眺望,立刻能够理解日本人在此处设立神庙的原因,这是一个从视野上扼两大洋的制高点。东方层层下降的森林把目光带向一大片沙滩,这是有名的港仔大沙漠,台湾人经常来开着沙滩车飙沙的地方,除此之外台湾东部大多是陡峭的断岩海岸。太平洋从这里看过去,与山同高,似乎抬腿就可以踏入海波。
向西方看,森林延展得更远,因为坡度较缓和,台湾海峡被推挤成天边一条蓝线。有趣的是,每一株相思木和大头茶都明显朝山下的方向后仰,保留着风来时的姿势,层层向山下倾斜,即使在这个没有风的春日,也雕刻出落山风的步伐。我心中真正理解了那首“月琴”里最悠长的两句:“落山风,向海洋;感伤,会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