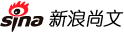教育有普世价值的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2日 09:15 新民周刊
“教育是有普世价值的”
《新民周刊》:总体而言,英美这些名校的课堂还是思辨的。但是我们的多数老师有时还是单方面的传声筒,学生是被排除在外的。
葛剑雄:其实我们并不缺少这种传统。上世纪30年代,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在燕京大学做研究生时,他就曾经指出他的老师顾颉刚在课堂上的错误,顾先生跟他写信,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最后顾先生非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把他们的往来信件当作补充教材在课堂中分发。
我在课堂上也会鼓励自由探讨。其实,中国有很多教授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问题是如何在体制上保证他们教学的自由。我想,教育是绝对存在着普世价值的,严格地讲,就是塑造一个“人”字。要鼓励他去追求真理,有时也意味着,他要挑战一个现有的真理。
《新民周刊》:确实如此,什么样的教育产生什么样的人才。
葛剑雄:是的。不过,什么样的社会,也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这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都是循环往复的。
从晚清以来,不少寻找真理的人,最后都想把自己的真理普及他人。所以,毛泽东当年说,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还加了一句,“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可能他年轻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跟他的这个方针并不符合,因为他的地位不同了。
《新民周刊》:学生们说,那些欧美的教授能把问题直接切入生活的横截面。而我们的不少高校教师要么就是照本宣科,要么就是不着边际。
葛剑雄: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中美两国缺乏可比性。据我所知,欧美混日子的老师还是有的,还得放到不同的教育体制下来考察。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我们还在编写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英美有这个吗?
我们有些课是硬性规定要上的,但是老师、学生其实心里都明白,这些课是毫无意义的。我校也有个老师想开一门课,后来被禁止了。那这是教授的问题么?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真正能落实教育传授知识、培养一个“人”的宗旨,那么很多问题,只是个技术问题。
现在学生逃课,也有些是根本不愿学。我就收到过一封学生的来信,说他根本不想上那个专业,是家里逼着上的。不上也不行,现在社会不公正,如果他爸不是李刚的话,拿不到大学的文凭,就找不到工作。
《新民周刊》:相比那些网课中的欧美教授,现在国内高校,有个性的名师很少。
葛剑雄:这个也要分开来看的。有个性的老师,那个中学教师袁腾飞,他的有些话我是反对的。他说“拿破仑绝对是个爷们”,这是给高中生上课么?“爷们”具体内涵是什么?大学的选修课可以,但是基础课,如果我是系主任,我是不允许这么上的。
在普通高校,有个性、有才华的老师注定不可能出现。要么他被更好的学校挖走,要么他所在的那个土壤也未必容得下他。这是毫无办法的。我们学校的3208教室以前是发布各种新奇观点的,现在还有吗?
在这个体制下,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无论是学术腐败、学风不端,真正的弊端在于权力对学校的干预。权力比金钱更加容易腐蚀大学。光是金钱,大学还不至于这样,大学经费增加,老师稍微有点骨气,还能抵挡得住。但是权力和金钱一结合,老师们就没有办法了。
《新民周刊》:您对中国的教育是十分悲观的。
葛剑雄:根本原因就是行政控制一切、腐蚀了高校。
比如说,中央党校的学历,教育部都不承认的,但是中组部承认。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党校学历,有本事你去念个正常的学校?重视这个学历,一是没有自信,二是权力控制一切。我们学校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谁都知道他就是个本科学历,谁敢嘲笑他?
“我们从没有过大学精神”
《新民周刊》:现在我们的高校除了教育的逻辑,还流淌着官场的逻辑。
葛剑雄:现在,行政机构掌握的钱或资源不受制约,以至于它的权力凌驾在学术之上。根源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泛行政化”。
现在的教授如果没有行政职位,还不如一个科长。现在一个小小科长都指手画脚,因为他掌握着资源。去行政化,是怎样保证学校有经费,有学术自由。
有些人成天谈这个问题,我笑他们太天真了,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你看朱清时去深圳创办南方科大,难得不得了呀!动不动就要去求当地政府部门,行政化只是换了个手段而已。如果这样,那还不如给他个行政级别算了。
《新民周刊》:跟欧美大学相比,我们的高校也存在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您怎么看?
葛剑雄:现在都在大惊小怪,说你们大学有钱,其实资金也没有增加到该增加的程度。我们的图书馆,英文书不如哈佛也也就算了,连中文书都输给人家,这说明我们其实没钱。所以,你给我几个亿,我也用得完。
现在大学的经费条款分割,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到了总经费的1/4左右,其余3/4来自各个项目和学校自筹经费。这个项目最后落到谁手中,你以为是评委么?在评委之前首先是一批行政官员。如果这些钱无条件发到学校,校长要去教育部“跑部烧香”?如果校领导无条件地分发到各个院系,我要去跟你磕头、拍马屁吗?
《新民周刊》:国外的私立大学也各有特色,但是我们的大学是被包办的。
葛剑雄:现在有的孩子,从幼儿园就送到外国去,每年几百亿、上千亿的钱就流到外国。如果是能够花钱在中国得到非常好的教育,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
教育不能包办,只能依靠市场。现在我们的收入差距这么大,应该容许增加学校,这实际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有利于穷人上学。有的国家规定,私立学校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经费让穷人也入校接受教育,或者拿出办学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捐给教育工程。这样,私立学校完全可以办成最好的学校。
对这些学校,国家只有监督的权力,没有管理的权力,比如监管它们的教育质量有没有达标。我们现在就莫名其妙地去限制民办大学的学费,这是不应该的,你给补贴了没?
《新民周刊》:现在国内不也在讲“教育家办学”吗?
葛剑雄:这又是一个空炮。现状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这到底为什么?!
我曾跟中央领导提过,请他们明示一下,到底哪些权归党委、哪些归校长?现在模式不一,得有个条文和规矩。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重建大学精神”这个话题?
葛剑雄:不是“重建”,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那会儿,清华的教授拉帮结派,你轰我,我轰你,也是经常的事,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么美妙。所以说,即使是教授治校,也要有好的体制保障。
我们现在连“教授治校”也不可能达成,最多就“教授治学”吧,各尽本分。
朱清时:中国高校硬伤在哪儿
我们做的这些实际上很多还是行政化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内容到讲课形式,并没有受到学生的热爱。所以光是宣布它是“精品课程”,这是不够的。“精品课程”是不是精品,应该由学生跟社会来评价。
记者/贺莉丹
从担任了10载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之后,朱清时依然壮心不已。去年,63岁的朱清时从2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以全票当选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也成为中国首位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而按照深圳的设想,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
办一所“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学,一直是朱清时的梦想。在他看来,这其实是回归教育的本原。现在,他正走在实践这个梦想的路上。
深圳的冬天很暖,在他居住的繁华一隅的一家政府宾馆套房中,朱清时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位“南下”的大学校长,将以此为家。这位中科院院士、国际知名化学家,川音浓浓,在直陈有关当下大学教育问题与弊端之际,常常眉头紧蹙,又总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清时担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不断呼吁终止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而在其他学校负债大兴土木时,中科大没有建新校园,同时也成为2000年以来中国唯一没有扩招的高校。对于教育体制的思虑,对于教育改革的探索,朱清时并不囿于某些纷繁现象的表层。而如果理性地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积弊所在,也许更能清楚地了解在一片国际名校的“公开”浪潮中,中国的高校所处的位置,我们的“硬伤”问题,以及我们的办学方向。
“敢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网课族”,学生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学习耶鲁、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些最好的教授的课程,包括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受哈佛学生多年追捧的“公正(justice)”,也成为网络开放式课程之一,而我搜索了一下我们中国高校的相关网络开放式课程,发现寥寥无几,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朱清时:我觉得,这是国际化的一个大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就开始把他们的教材公布在网上,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教材是可以共享的,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密或者说这是学校的专利,他们认为教学的成果应该是全社会共享的,所以他们乐意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敢这样公开他们的课程,也是出于他们有很大的自信心,他们觉得他们的教材、课程好,他们才敢这样做。而如果没有自信心的学校,把教材、课程放到网上,别人看了以后挑出很多毛病来,那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所以,敢这样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而且,把课程放到网上,也是对学术的一种监督,别人也可以提意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
哈佛大学的那门关于“公正”的课程,我也知道,我希望我们南方科技大学学生的全面教育也有这样一些课程。我们会请到一些优秀的学者来讲课,我很想让学生去听这些课程,比如,关于“幸福”的课程,或者是关于“兴趣”的课程,我都愿意给学生讲。因为我一生中间,对很多事情我都很有兴趣,比如看文物、书画、陶瓷,我想要告诉学生:生活中间多一些兴趣,你的生活将更丰富,而且智力可以开发得更好。
这些课程是过去大家不太重视的,大家过去以为只有知识才重要,实际上还有比这个知识更重要的,那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我觉得,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和他们现在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当然他们这么做,我很欣赏,但这还是教育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它。我们现在首先是做招生、建立我们的教学大纲这些工作,等到学校的工作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考虑这种开放式课程,现在我们是想改革教育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新民周刊》: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华裔退休教授向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推荐这种开放式课程计划时,一些人上来就质疑他,“为什么这样做?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吧?”你觉得这跟我们的接受心态有关系吗?
朱清时:是的。这个公开是:第一,学校有自信心才敢公开;第二,它公开是因为希望它的成果能够被全社会共享;第三,它公开是因为它希望大家能帮它提意见,如果有人能够挑出毛病,它就可以改进,所以公开实际上是一个提高教学质量的好办法,并且让它的教学成果能够被更多的人分享。所以,认为“有什么目的”之类的,这种观念很狭隘。
《新民周刊》:比如,耶鲁大学教授谢利·卡根的“哲学:死亡”一课,让很多中国的学生感到新鲜,这位教授盘着腿坐在讲桌上大谈哲学。现在我们教育部也设立了一个“全国高等院校精品课程建设”,为什么在实际效果上它比较少受到学生的追捧呢?
朱清时:我们做的这些实际上很多还是行政化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内容到讲课形式,并没有受到学生的热爱。所以光是宣布它是“精品课程”,这是不够的。“精品课程”是不是精品,应该由学生跟社会来评价。
《新民周刊》:对于这种免费的网络开放式课程,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就曾经投了很多钱进去,MIT时任校长查尔斯·威斯特直接推动了这个计划。在你看来,大学应不应该从经济成本上考虑这件事情?
朱清时:其实大学都是要考虑钱的问题。但是,这个公开,对MIT也很有利益的,能够提高他们学校的知名度,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他们的眼光更长远。
“整个中国大学的风气都是崇尚研究而轻教学的”
《新民周刊》:事实上,如果想要公开,现在中国的高校并不缺这个技术。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学生感叹,“当哈佛、耶鲁将最受欢迎的课程主动放到互联网上时,我上学期却有一门课的老师连电子版讲义都不愿拷贝给我们,这种差别太鲜明了”。
朱清时:1994年,我从国外回来,回到中科大,1998年我担任中科大校长,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学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比起国际一流大学来都非常落后,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就是缺包括我们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怎么讲课这些技术,当时我就组织学校的很多人到国外去考察,我带了一些人考察了欧美很多一流大学,想引进他们的这种教学方法,包括你说的他们大学的这种公开课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推不动。
《新民周刊》:为什么呢?
朱清时: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表层问题。因为教授们没有积极性,没有制度驱动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往往都喜欢做自己熟悉的事情,或者少费力气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高校教育想要上去,首先是人才,所以我就开始引进各种各样的人才,花了大概七八年时间,中科大跟中国其他一流的高校差不多了,教师队伍基本上都是有国外工作、留学背景的。我当时以为,只要有了这些人才,他们自己会琢磨这个课程应该怎么上的问题,比如,这个课程是不是应该公开?老师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他才会想;而水平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老师,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而且他也没有积极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发现,这些国外的人才虽然回来了,但是渐渐地,他们也不太关心怎么教学了,而是关心上级有什么意图、关心当官了……这些有国外工作、留学背景的老师也很快就被国内的文化给同化了。
所以,在老师并没有去动脑筋教好课的情况下,你讲的这些技术问题,都是白讲。他们的心根本就不在那儿,他们还要去竞争项目、竞争经费、提职称。他们要提职称跟竞争项目,首先是SCI论文要发表多少、或者是要多少成果奖,于是他们就要去寻求多发表一些论文、成果奖多一些,为此他们就要去做很多社交工作、做很多研究以外的工作,他们的心思就不在如何把这个课程教好或者把效果教到最好上了。很多老师就已经并不是热衷于教课,而是热衷于搞科研发表文章了,而且搞科研也不是他们自己去搞,他们招了一帮学生来搞,然后去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运作这些成果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像你说的这个问题,还是表层的。
《新民周刊》:当时在中科大范围内有没有设置一些学校内部公开的由优秀教授主讲的课程?
朱清时:学校里面也有这种课程。
《新民周刊》:后来它们推广的效果如何?
朱清时:并不是很理想。因为整个中国大学的风气都是崇尚研究而轻教学的。有关教学的任何事情都是量化了来评估的,教学的重要性就体现不出来了。当时我们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做下去,就是因为教师并没有内在的动力去推动课程改革。
《新民周刊》:就是说这个从欧美一流大学取经的课程改革的受挫,折射的其实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
朱清时:真正的是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南方科技大学要做的“去行政化”,要让学校恢复到它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教授治校、学术主导”,要用机制去促使老师们去把教学、科研做好,而不是光看老师们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这些。而只有有了这个机制,慢慢地,老师们才会去想如何把课教好,在讲好课之后,在某一个高级的层次上,他们才会想教材、课程要不要公开的问题。
“名气高的大学是生源好,而非教学好”
《新民周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讲课讲得好的老师不一定升得上去,很有名的教授讲课我们不一定爱听”,你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
朱清时:很有名的教授不一定课讲得好,这是因为这个“有名”是他做研究有名或者他社会地位高,而他的社会地位高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参与各种活动的原因,所以你说的这个“有名”是在现在中国语境下的“有名”,比如,他当了职位很高的官了,那么他就变得在媒体上很有名了,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问就有那么高。讲课跟媒体上有名是两码事。
而如果这个教授是讲课有名,那他的课就一定要讲得好,过去在我做学生的时代,就有好多教授是讲课很有名、也讲得很好的,那个时代的复旦、北大、南京大学、中科大都有一批老教授,他们讲课讲得很好,他们也没有做过什么科研,但是我们都一直怀念他们。现在,这种教授越来越少了。
《新民周刊》:这是为什么呢?
朱清时:这是我们的体制啊!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的评价体制过多地强调发表论文,强调科研成果,强调经费,老师的讲课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所以,讲课讲得好的老师反而吃亏,而那种不务正业、不讲课却在外边拉关系、争项目,成果奖、SCI论文弄得多的人就变得很有名、很有地位了。这种体制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现在的大学真正科研做得好的教授,教学很少,往往教学的都是一些年轻的没有太多履历的人,所以往往就教不好。
《新民周刊》:你认为我们目前的高校体制里面,评价一位教授的主要标准是哪些?
朱清时:现在评价一位教授,就是看他论文有多少,成果奖有多少,经费有多少。
《新民周刊》:那他给本科生上课这一块呢?
朱清时:这是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间很不受重视的一块。
《新民周刊》:其实我们的大学某种程度上是鼓励这么做的,对吗?这其实对大学来讲也有好处。
朱清时:对,我们的大学一直在鼓励。
《新民周刊》:我们通常讲,做学问是一个相互砥砺的过程,而现在我们的我们许多高校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互相保密,而不是互相公开,你是怎么评价这种风气的,它健康吗?
朱清时:当然不健康。现在各个大学必须相互都要公开,包括公开课程、讲课内容这些,这样才能够真正竞争。现在我们的大学对这些没有公开,那竞争就谈不上了,所以最后往往都是看这些大学的名气。
我们的名气高的大学,它就能够招收到最好的学生,而学生水平好了,老师讲课讲得再不好,学生也自己会学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好大学实际上是靠收好学生来维持它的水平的,而不是说它的教学有多好。
《新民周刊》:能讲讲南方科技大学招的这个10岁的来自山东泰安的“神童”吗?
朱清时:这个小孩不能说是“神童”。他今年10岁,从小就喜欢看教材,自学能力很强,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把小学的课程都读完了,老师叫他去上中学,中学上了一年,他把中学的课程也都自学完了,老师又叫他去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高考,结果他考了566分。我们对他进行过详细的测试,他的知识也有严重不足,有些知识也很缺乏,但是他有些数字方面的能力很强,他的记忆力很强,他的想象力也很强。这样的小孩,如果环境好,他有可能成材;如果教学不得当,他也可能很快就被埋没,和普通人一样了。
现在的大学都行政化了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有很多高校都宣称要建“一流的大学”,这样的口号我们并不陌生。在你看来,一个一流大学的大校心态应该是怎样的?
朱清时:中国首先应该建真正的大学,然后才是建一流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很多大学都不是真正的大学。所谓不是真正的大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实际上都官僚化了。
大学本身应该是一个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学术至上的机构,但是,现在我们的大学都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不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这样的团体、这样的大学,实际上已经官僚化了、行政化了,这种大学就没有生命力了,因为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就照官大的人的主意来办学,那么很多创新的思想都不会得到成长,就容易没有朝气跟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钱学森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现在的大学,首先是要把体制改了,就是让这些大学真正成为一个学术团体,大家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当官,或者是谁的官大就听谁的;第二,让一些好的教授进来,因为好的教授进来之后,他们自己就会下功夫去钻研怎么把教学做好,这个时候学校再因势利导帮助他们,那他们自然就会把教材、教学方法搞好了。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目前中国的高校在跟全球交流的时候,我们欠缺的是什么?
朱清时:中国的高校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外籍教授,中国的高校距离全球化还甚远。我们最多的留学生可能是北大这样的学校,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学校,留学生也基本上是来学中文、学中国历史这些跟中国有关的课程的,还没有很多留学生是来学物理、化学、数学这些课程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高校很少用英语讲课,大都用中文讲课,这样就有语言障碍。现在不得不承认,英语还是科技界的国际语言,如果一个高校要国际化,你要多用英语讲一些课,学生的英语水平要足够高,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外籍教授、留学生来,他们来了,才会带来不同的文化,学校才能够真正的国际化。
《新民周刊》:今天我们依然会感叹诺贝尔奖跟中国无缘。作为教育者,你是怎么看的?中国的大学的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朱清时:现在首先是,我们的大学还是这样死气沉沉的,我们的学校还是很官僚化、行政化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活力的大学,这个时候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现在我们的大学都官僚化、行政化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
举个例子来讲,大学就应该像过去的梅兰芳剧团,梅兰芳他们就是为了唱好京剧,只要梅兰芳能够唱好京剧,他们京剧团就做各种事情帮助他,他们就是这个目的。后来京剧团变成政府机构了,政府设了团长、副团长这些级别,这些京剧团就行政化了,梅兰芳名义上是团长,但是也官员化了,他的戏就再也唱不好了。官员化就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包括梅兰芳要做什么事,这些官员就觉得想支持你就支持,不想支持你就不支持。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的。
《新民周刊》:两年前钱永键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国人很激动,感觉诺贝尔奖让华人获得,也算跟中国有了某种渊源。但其实我们还是一个旁观者。
朱清时: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得要做教改。华人在国外每次得诺贝尔奖,我觉得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鞭策,为什么他们在国外就能够诺贝尔奖?为什么我们本土就没有呢?
《新民周刊》:我们的应试教育根深蒂固,学生上课也往往是灌输式的而少有互动。作为大学校长,你感觉到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一些伤害了么?
朱清时:应试教育让学生变成考试的机器了,当然这对学生是伤害很大的,这样学生就对科学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了,这样学生的创造能力肯定就会受到抑制,不会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