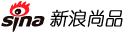龙应台:自由不自由都是我的选择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21日 09:35 外滩画报 微博
5月20日,龙应台将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相比13年前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现在的她“EQ高了很多,身段变得很柔软”,比过去“暖”了很多。
 龙应台
龙应台5月20日,龙应台将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2月15日,她正式就任台湾“文建委主委”,此后该委将改为“文化部”。相比13年前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现在的她“EQ高了很多,身段变得很柔软”,比过去“暖”了很多。
文/刘牧洋 发自台北 编辑/吴慧雯 摄影/杨少帆
4月18日,龙应台起得很早。这几个月来,她一向如此。如果不失眠,她通常会早醒,因为每天的会议常常从早上8点一直连续排到下午6点。
早上7点半,她到达台北车站搭乘高铁,有一个特殊的“会议”在等着她。33分钟后,新竹县文化局长蔡荣光在新竹高铁站看到了她的身影。
对蔡荣光来说,这是迎接“长官”的到来,更是老友的重逢。13年前,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和他时常碰面,共同参加文化局长会议,他们当时戏称为“同学会”。一个月前,龙应台找到他说:“不如我们再搞一个‘同学会’?”
于是,全台湾各县市22位文化局长,还有即将合并入“文化部”的“新闻局”、“研考会”等单位,都收到了龙应台的一张“同学会”邀请函。
这一天是台湾有史以来文化领域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官员聚会,也是龙应台上任后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此时,距离龙应台上任“文建会主委”两个月,离台湾“文化部”的挂牌成立只剩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悬念,龙应台即将成为台湾第一任“文化部长”。
这不是龙应台第一次为官。早在1999年,她曾经接受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的邀请,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那一次的她顶着“文人从政”的帽子,在众人的目光下,冲冲撞撞做了四年。
任期结束后,她毫无留恋地请辞,重归自由之身,去香港教书,继续写作,出版了《目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作品,没人预见她会再回政坛,但她却回来了。
一直强调自由的龙应台对《外滩画报》记者坦言:“确实,我现在非常的不自由,没有时间写作,也不能随时去大陆。但我个人的自由或者不自由,没有什么好埋怨,也不能嗷嗷叫,因为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怕热不要进厨房”——这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名言——在台湾流传甚广,意思是如果吃不了这份苦就不要做这件事。“我日子过得好好的,如果不是有点理想,干吗做这个事,钱那么少,压力那么大,还要被人骂。”
在“同学会”上,龙应台这句话说出来,在场的文化局长不少为之动容。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好奇,为什么这几个月没有见到我,因为我的头根本伸不出来,我们都在厨房里忙碌。我也知道很多人包括评论家们都在期待我们会端出什么样的菜,但现在菜没有做好,我还不能说。”龙应台说。
5月20日,是考验这个用惯了笔的“龙部长”厨艺的时候。
马英九的奇招
台湾的官员不好当,“文建会主委”更不是一个好当的官。“文建会”全称为“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是台湾文化事务的最高主管机构,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特别是在“梦想家”事件爆发后,“文建会”主委一职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烫手山芋。2011年,为了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台湾“文建会”委托表演工作坊制作了一出摇滚音乐剧《梦想家》,耗资新台币2.15亿元。
此剧一出很快引发台湾社会内部的激烈讨论,认为此剧费用过高、财务账目不清, “文建会”是拿纳税人的钱做政治秀,“梦想家”事件成为一个政治弊案。2011年年底,时任“文建会主委”的盛治仁在巨大压力下请辞,由“政务委员”曾志朗接任。
但这并没有打消人们对“文建会”的批评与争议,“曾志朗当过‘教育部长’,也当过学校校长,他一直在努力推动阅读运动,他这样的资历和努力还让很多人觉得他不够文化,不能做‘文化部长’。”台湾《时报周刊》社长夏珍说。
据曾志朗的太太洪兰向友人透露,自从当上“文建会主委”,曾志朗便吃不下睡不好。今年1月,曾志朗请辞。
谁是最合适的人选?谁又能坐稳这个位置?加上“文建会”要在5月升级成“文化部”,这个权力突然变大的空悬职位成为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此时,远在香港的龙应台正在悠闲地喝茶写字,享受和儿子在一起的生活。
她已是香港大学教授,在港定居近十年,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她描述自己的家面对大海,早上一起来,第一眼看到的是无边无际蓝色的天和海。“有很大的空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当时的她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在接下来的某一天,留下一杯还在冒热气的茶,一堆待洗的衣服,放弃平静的生活,这样抛家弃子地跑回台湾去。
“我当时就在想,马英九会不会出奇招,把龙应台找回来;而龙应台如果要出马,必须要马英九亲自去请。”和龙应台认识三十多年,从媒体人转型为政务官的台中市文化局长叶树姗说。
龙应台对马英九是怎么请动她的避口不谈,但她与马英九的深厚交情早为人所知。2007年,马英九涉特别费案,龙应台在媒体发表文章为马英九辩护。2008年台湾“大选”,龙应台专门回台湾投票支持马英九,最后却因为不熟悉投票规则,用私章代替投票章,使自己的选票变成了一张废票。
“朋友有两种,一种是天天在一起吃喝玩乐的;一种是并不常见面,但在你需要的时候,她总是会出现。我觉得马英九和龙应台是后一种。”叶树姗说。
龙应台上任“文建会”的消息一出来,很多人在惊讶的同时,也认为她是最合适的人选。
三年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对台北做了一番“隐性”的文化建设。她不热衷于砸大钱,而相信细水长流;她不太会盖新房,而是悉心保护了很多老房子;她重视台北的城市特质,为台北开创很多文化“村落”,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
“因为大家都知道龙应台的个性,对她很放心,知道不可能再出什么弊案。而龙应台在台湾也有一定影响力,很多人还是顾忌她几分。”夏珍说,龙应台的上任,成功地降低了人们对“梦想家”事件的质疑声浪,加上龙应台粉丝众多,一些文化局长也是她的读者,配合度就更高了。
当然,也不乏有人猜测龙应台之所以放弃轻松安稳的生活,趟这个浑水担任“文化部长”,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资历,因为做了“部长”出去,身份就不一样了。
黑与白
在台北的一周,我见到了龙应台两次。一次她穿着黑白条纹T 恤配黑布裤子,外面套一件黑色小西装;另一次是白色衬衫配黑布裤子,腰间都绑着同样一根男式宽牛皮带,衣服扎进裤子,袖子挽起至手肘。若是仔细观察一下龙应台以往的照片,可以发现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黑、白这两个颜色。
这也是一直以来,龙应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性格色彩。她个性率直,似乎只有黑和白,没有灰色地带。上世纪80年代,当她因写批评文章而声名鹊起时,曾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胡美丽坦言:“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龙应台初入文坛时,25岁的台湾媒体人叶树姗正在主持一档广播节目《书香社会》,她在《新书月刊》上看到了《龙应台评小说》的连载,对这个署名为“龙应台”的作者很感兴趣,便打电话给《新书月刊》的创办人周浩正,希望能请这位“龙先生”来上她的广播节目。
“结果周浩正告诉我,这位不是龙先生,是龙小姐。我很吃惊,因为她的文字是那么男性化。”当时,很多人都以为龙应台是男的,直到见到龙应台,叶树姗发现,她和一般女性的确有些不同,“有点严肃,说话很直,并不喜欢笑,而且因为她写批评文章嘛,总要有点端着的感觉。”
“她那时还没有写《野火集》,并不太出名,只是在学校里当教授教书,也没有去德国,都还没嫁人,还是个小姐。”
也许是不习惯自己在镜头面前的样子,龙应台不喜欢接受电视媒体的访问,她只愿意接受报纸采访,或上广播节目。叶树姗后来进入电视台当主播,主持电视节目《一念动大千》,想访问龙应台,被她婉拒,理由是“觉得自己面对镜头会不自在”。
1999年,在“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大力推荐下,马英九前往德国把龙应台请回来当台北“文化局长”。没过多久,叶树姗邀请龙应台和周浩正吃饭,大家故友重逢,龙应台很是高兴。“她当时刚当台北市‘文化局长’,还不太适应官场的文化,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她说到孩子在德国的成年礼,因为她台北的工作很忙,没办法回去参加。”说着说着,龙应台不禁感伤起来,眼泪突然滚落出来。
一面是对儿子的思念之情,一面是她不熟悉的政治生态,在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文人龙应台怀着“大破大立”的一腔热血就这样闯进了政坛,难免磕碰,最后发出“大破易,大立难”的感慨。
2011年,从媒体转型为政务官的叶树姗在台中大甲的一次饭局上,碰巧和马英九同桌,马英九问起她是否适应政治圈,叶树姗便诉说起民意代表的压力。马英九笑了,搬出龙应台来举例:“你要想想当年的龙应台啊!”
当年,政治新人龙应台遇上“磨刀霍霍”的台北市议员,第一次交锋就让人印象深刻。在议会上,市长马英九站在答询台,议员们一个接一个问题炮轰,“你为什么要找龙应台?”“她来自德国,不是台湾人,你凭什么认为她适合?”一旁的龙应台实在忍无可忍,最后从座位上直接举起手来,大喊:“我抗议!”这个举动轰动一时。
“马英九的意思是,你看连龙应台这样有棱有角的个性,最后还是忍了下来做了四年。”上个月,叶树姗遇到龙应台,提起旧事。聊到当年的自己,龙应台也笑了。
这次再度出发的龙应台忆及当年,颇为感慨:“做官,要达成一件事情,80%在与人的协调上,这个基本道理我快50岁才认识到。”
上任“主委”后的第一件事,龙应台主动拜会“立法委员”,这让有些原本严阵以待想要刁难的“立法委员”很惊讶,认为她和以往不一样,低姿态且和善。13年前当“文化局长”时,她第一个月就和市议员吵得不可开交。而这次她上任两个月,和“立法委员”相安无事,一团和气。
“我觉得她这次回来笑容多了,脸的线条柔和很多,不像她当时回来当文化局长的时候,线条是硬邦邦的。她的EQ高了很多,身段变得很柔软。以前有人误以为她骄傲,她只是有她的作风和想法,不愿意去迎合别人,她的直接可能会让人有压力。她现在也不是要去迎合别人,只是学会了用什么方式去沟通。”叶树姗说。
让叶树姗更觉得有趣的是,这一次故友重逢,龙应台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讨论业务,而是好奇地惊呼:“你脸上怎么都没有斑?”那一刻,龙应台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当然,总会有人不服。“同学会”上,云林县文化局长李明岳毫不客气地问她:“你把我们找过来,预算什么的都不知道,那找我们来做什么?”
换作是以前的龙应台,也许她早就跳了起来,直接抱怨说:“你现在问我,我也没办法给你答案啊,我现在还在厨房里忙碌呢,你要给我点时间!”
现在,她很耐心地回答李明岳:“你要有同理心,如果你是有65年历史的‘新闻局’,要并入只有30年历史的‘文建会’,你的心里会怎么样?所以给我一点时间吧。”
“一样要对方给时间,但她用的方式是‘please(请)’,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制造对立。我觉得她已经想清楚了,这一次的龙应台做好了准备,她给我的感觉是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愿意展现全部的自己。”叶树姗说。
龙应台在台湾有几个老友,只有在他们面前才会流露出自己的脆弱。其中一个好友是亚都丽致饭店的总裁严长寿,每当龙应台心情不好的时候,严长寿便会为她在亚都饭店留一个角落,让她安静下来。
“同学会”结束后,龙应台随众参观萧如松美术馆,她站在一棵野生的芭乐树下,有人看到果子长得好,伸手摘了一个下来递给她看,没想到她拿起来就往裤子上一擦,张嘴便咬,完全不顾身边人的惊呼:“不能吃,里面可能有虫!”
吃到一半,果然发现有虫,她吓得跳起来,赶紧把果肉吐出来,到处找垃圾桶要丢,惹得众人大笑。这一面的龙应台,在十年前,你没机会看到。
从村落文化出发
“我本来以为那一缸满满的都是米,结果走进去,发现一半都不到。进了厨房,你才发现这个那个问题,只得带着心里的热情,闷头在里面做菜。外面的人是不知道里面的厨房是有多小,菜有多少。”尽管有了经验和心理准备,龙应台还是面临了很多没有想到的状况。
龙应台曾拜访过夏珍等媒体人,和他们交流。毕竟她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局,而是编制近300 人的“文化部”。“我觉得她还是有点紧张和焦虑。”夏珍说。
龙应台坦承,要建立一个新的“文化部”,和13年前建立第一个文化局的开疆辟土太多不一样,“那时只是单纯的辛苦,从无到有地垦荒。而现在是要把运行了65年的‘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部门,加上35 年历史的‘文建会’,组合在一起。”
她这样描述自己面临的处境:“我现在的感觉是身上紧绷四件大小不一的衣服,有的套紧了你的手,有的套紧了你的腰,有的甚至绕在你的脖子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你还不能把它脱下来,你需要把它们重新缝成一件衣服,一件符合社会期待的、端庄的、好看的、有时尚意义的衣服。”
位于台北市北平东路上的“文建会”如今正在装修,原本是很小的一幢楼,招牌隐藏在楼底,很难引起人们注意。壮大后的“文化部”人员如何塞进这幢小楼,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而如何设立新的职能部门,让它成为一个有效运作的体制,也是一大考验。
但人们最期待的是,文化人龙应台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文化?她给的答案是“村落化、国际化、云端化,从村落出发,从国际归来。”
尽管是外省第二代,但龙应台一直在台湾乡村长大,她自称是“台湾乡下人”。“我在高雄的大寮出生,在茄度过我的青少年时期,后来跟爸爸去苗栗泰安的象鼻村,那个地方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开车可能都找不到地方,所以我是完全的村落的小孩。”
龙应台对村落有着特殊感情。1987年,已经因《野火集》名声大噪的龙应台离开台湾,住进了德国一个两万人口的村落。这个村落让她很是惊喜,“村里只有一条街,从头走到尾,一共三个小书店,里面书不多,但是你在电脑里输入任何一本书,系统里面都有。这意味着如果你要买任何一本书,24小时就可以送到手上。”
除此之外,这个村落里还有一个完整的表演区域,甚至乡公所就可以直接办理护照和签证。
八岁的孩子放学归来,问起她阿富汗的事情,“为什么打仗?”她很惊讶儿子年纪这么小就对这个感兴趣,最后她得知,是因为儿子班里来了一个新同学,是阿富汗难民。“他所在学校的孩子来自韩国、阿富汗、日本、美国等各个国家。对这样环境里的小孩子而言,国际化不需要努力去教他。他问你阿富汗的问题,不是要了解全球化,而是要了解自己身边的小伙伴。”
“我隔壁有一个80岁的老太太,是我的文学情报站,她每天读法兰克福报纸,然后向我汇报,哪一个作家会来村子里签字。”最让龙应台吃惊的是,有一次家里年近60岁的打扫阿姨突然向她请假一天,说要去法兰克福的音乐厅看《蝴蝶夫人》的演出,这让她震撼很大。“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村落文化能高度发展成这个程度?”
她带着这样的疑问来看台湾的文化发展,想起2000年时,她还在当台北文化局长,带着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到云林县的公园里演出。下乡前,有同仁担心,“云林那边的乡村会不会有人懂歌剧这样的艺术?”去的时候下起大雨,他们准备了雨衣,也准备了冷场的心情。没想到演出时,公园里铺天盖地都是人,那些脸上刻画着农作沧桑的农人站在雨中一个半小时从头看到尾。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嚼着槟榔、脚趾里还藏着黑泥的男人走过来对龙应台说,“局长,这出没什么好看啦,你什么时候把卡门带来才算数。”她才惊觉有可能因为大家的成见,而忽视了乡村的文化,“我们一直把乡村当作城市的附属品,重大的建设都放在城市里。但文化就应该从乡村出发,让它变成繁星点点,用文化富民。”也正因如此,她没有把上任后的第一个“同学会”办在台北,而是放在了新竹。
龙应台并不肯透露她在两岸文化交流上的具体措施,但她也主张以民间的交流为主。
对于台湾的文化建设和龙应台的思路,台湾作家李敖的意见更尖锐:“台湾根本没有文化,那些乡村的东西不能算文化,‘文化部’就不应该存在,更不要谈什么‘文化部长’。”
李敖(微博)曾经写了整整一本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指出龙应台近年来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的不实之处。“我现在有点后悔,犯不着特地去写一本书骂她。”李敖对《外滩画报》的记者说,他说,尽管龙应台不懂中国近代史,但“她算是一个有才气的人,只是不应该去做什么‘文化部长’。”
(【新浪尚文-文化艺术】栏目欢迎相关机构合作邀请,详询010-8224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