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从彼岸到此岸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26日 08:23 国际先驱导报 微博
如果带一本书来2012,《2666》也许是不错的选择。正是这种无意而为的隐秘前瞻性,令《2666》神奇地具备互联网时代的超链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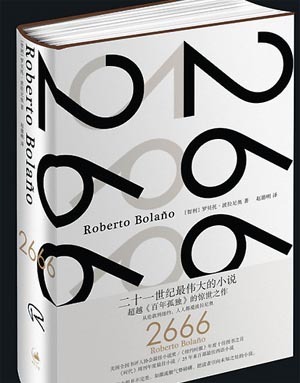 《2666》
《2666》《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在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并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以一本书的名义相聚,他们交谈,并为交谈中所产生的火花兴奋不已,他们试图在某个文学的分枝上徒步,并因有所前进而欢呼雀跃,那一刻,窗外的冬天可以退得远远的,连生活本身都只沦为背景。
也许是因为它的魔幻性,或者文学之外的某种力量,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使以上一切得以发生。2011年年底,作家余华、电影批评家戴锦华、独立戏剧制作人牟森、诗人胡续冬、西语翻译界前辈赵德明、书评人止庵等人在同一个下午出现在智利大使馆,以各自的阅读体验和批评,向波拉尼奥致敬,而在“带一本书去往2012”的可能性面前,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2666》。
更为巧合的是,眼前的这一幕似乎就是波拉尼奥《2666》第一章某个段落的再现,也正是这一章,揭开了这本魔幻而浩瀚的小说中几个文学评论家的漫长历险,而他们历险的前奏,恰恰开始于一次以神秘作家阿琴波尔迪为名的聚会。在戏剧制作人牟森的“气象学结构”的思维里,这四个文学批评家便是追赶龙卷风的气象学家,他们要找到风暴中心,而神秘作家则引着他们上路。
文学之中的文学
翻译这本厚达872页、从内容而言营造出多个层级世界的小说并非易事,北大西语系教授赵德明先生说,他把翻译这本书当成一个博士后工程来做。作为曾最早将诺贝尔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译介到中国的西语专家,赵德明坦言多年后与波拉尼奥的相遇无疑是另一次“神奇的体验”。“这本书信息含量太大,历史、军事、心理、犯罪、海洋等等无不涉猎,中间甚至穿插一段对于遥远中国的描摹,简直是奇思狂想,但同时又如此冰冷。”
感谢自己曾经的智利留学经历,赵德明才没有被淹没在波拉尼奥的狂想海洋中。也正是翻译过程中对于波拉尼奥一生的探索,令赵德明发现,有那么几个坎一直萦绕在波拉尼奥的笔尖,而这几个坎,成为最终联系波拉尼奥与文学的最坚固脐带:“一是1973年,阿连德总统的合法政府被武装推翻,一批文学青年逃离;二是1968年墨西哥广场对学生的镇压;三是苏联解体,那种不知道该上哪去的迷茫。”在赵德明看来,波拉尼奥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通过文学来纾解他们从时代那里受到的伤害,“他们甚至已经超越了文学”。来自文学的投射,也体现在《2666》的很多细节里,它显示的并不是文学范畴的问题,也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永恒的问题。它给出的信息太多了,但是给出的信息也太少了,因为它只是一双眼睛,正如一切都将走向“生活在当代之艰难”这个议题。
正是这种无意而为的隐秘前瞻性,令《2666》神奇地具备互联网时代的超链接性。“你看《2666》里在描写墨西哥黑帮、在描写人们面对暴力时候的态度,就可以感觉人与人之间,那样一种戒备、防范、冷漠,这就是它的全球性。”
世界的公民
“在过去的10年里,世界范围内被谈论最多的西班牙语小说不是《百年孤独》,而是《2666》。”作家余华见证了这一点,2008年他去法国宣传《兄弟》,书店里放着的唯一比《兄弟》还厚的就是《2666》,2009年再去美国,书店里看到的还是《2666》。“无论在法国、还是美国,你只要问《2666》是什么书,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甚至告诉你它的故事是什么。”
但尽管如此,余华并不同意把《2666》和《百年孤独》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波拉尼奥完全是一个世界公民,“他是到了什么地方都可以扎根的人”,但马尔克斯还是一个小镇居民。“而且我一直不太同意哪本书超越了哪本书,或者哪个作家超越了哪个作家。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此它像森林一样,波拉尼奥是一棵大树,马尔克斯也是一棵大树,树和树之间不存在超越,文学之间则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你需要我,我需要你,作品和作品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波拉尼奥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以后,可能会唤醒一些非西班牙裔的知识分子重新对马尔克斯和早一辈的拉美作家感兴趣。”
如此说来,波拉尼奥也许应该感谢马尔克斯,“如果没有他们那一代人,拉美文学恐怕直到今天也难出头。”但另一个事实是,波拉尼奥所面对的世界,早已不是马尔克斯的世界。
生命的状态
毫无疑问,《2666》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波拉尼奥本人的多层次性。诗人胡续冬将波拉尼奥视为“一生苦闷的青年”,“但他和我们理解的愤青不一样,虽然在骂,但是他的‘活儿’很过关,他的‘愤’和他的‘活儿’是有效的结合在一起的。”
胡续冬将波拉尼奥的小说总结为“文学之中的文学”,那是因为“他在一个小说里面能够层层嵌套很多真真假假的东西”,而我们同时不能忘记的还有,波拉尼奥其实还是个诗人。“真正的诗人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他说他的写作一定要像游击队员一样,一定要像不明飞行物一样,要像终身监禁的犯人的眼睛里游离不定的眼神一样,其实他的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假人,这个人是他的名字的转化,比如波拉尼奥转化成的阿图罗·贝拉诺(《荒野侦探》的主人公之一)。”
或者,在电影批评家、北大教授戴锦华《2666》的阅读中,波拉尼奥成为阿琴波尔迪,“尤其是我们以评论家的身份在这里时,就很像第一部分当中那些有点滑稽、苍白的,甚至有某种伪善、脆弱的当代知识分子,至少我们在他的镜子里照见了自己——我们还有救。”
也正因此,对于戴锦华而言,阅读《2666》几乎是全新的文学感受,“它言说出后冷战,后革命时代的人们——没有那么心甘情愿的加入成功者,加入角逐成功道路当中——仍然带有梦想的人民,而这种梦想却没有严肃的合法性。”
准确地说,这是波拉尼奥所传递的文学状态,而它和格瓦拉的在路上不一样,后者是周而复始的,而波拉尼奥的旅途是徘徊的,是一个没有路标的行程,是不到达那里。“我像是被突然打了一巴掌,得以看清这一生命的状态。”戴锦华说。
(【新浪尚文-文化艺术】栏目欢迎相关机构合作邀请,详询010-82244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