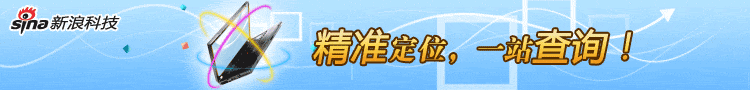洛丽塔之父纳博科夫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18日 08:45 经济观察网 微博
纳博科夫的文字,真是充满了声、光、色、味觉、触觉,还富含隐喻、象征、幽默,以及对觉知、时空观、失与得、政治流亡、思想自由等种种人生问题的哲学思考。作为读者,我们真得平心静气,开启我们所有的感官,张开我们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地欣赏和理解《说吧,记忆》。
 洛丽塔
洛丽塔范玮丽
总觉得我与纳博科夫有缘。
初识纳博科夫是上世纪80年代,在导师巫宁坤先生的阅读课上读了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节选。
1986年,随巫先生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届美国文学年会,有幸面会了许多仰慕已久的英美文学前辈,比如杨周翰、戈扬、冯亦代、毕朔望等等。他们几乎个个饱经风霜,历经种种政治运动洗礼,不是去过北大荒、劳改营,就是进过牛棚、五七干校。劫后余生,相聚在这个文学的春天的盛会上,他们谈笑风生,意气风发,大有返老还童,壮心不已之势。那个场面,至今令我难忘和感怀。也许是为巫宁坤先生的诙谐风趣、爽朗笑声打动,有个年轻人问巫先生,回国后受了那么多的苦,九死一生,您就没有怨言吗?巫先生答,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没有幸免,而我活下来了,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作为先生的学生,我从先生身上学到的远远不只是学问。
会后,承蒙李文俊先生信任,约我为《世界文学》翻译纳博科夫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初次接受如此重量级的杂志约稿,欣喜之余难免为自己译文的青涩担忧,于是拿着译稿登门请毕朔望先生批评。毕老热情相助,将译稿与原文对照,认真校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译文“信”有余而“雅”不足。经毕老润色过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在《世界文学》刊出不久,我又接到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约稿,为三联书店计划出版的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翻译其第一篇《简·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
1987 年交稿后我便赴美留学。那是没有手机、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生活拮据的留学生涯,搬家频繁,学业繁重,很难通过书信保持联系。对于我的纳博科夫译稿下落,我始终一无所知。但每当我在书店、图书馆或文学课上遇到纳博科夫,总像邂逅老朋友一样高兴,同时又心生感激——是纳老让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
2005年,我们举家搬迁北京之后,我曾经在地坛书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三联书店的书摊、展柜前寻找与纳博科夫有关的书籍,皆一无所获。我猜想,文学类书刊最终没能按计划出版并不罕见,也许我的译稿早已葬身于废品回收站的废纸堆。
2010年十一假期,我在香港突然接到新朋友丹娃短信,说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一本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其中两篇译者属名与我同名,“是你翻得吗?”我又惊又喜,20多年,音信全无,居然被丹娃意外撞见!古人说的真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丹娃还告知,书是2005年4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我心中纳闷,1987年的译稿,何以18年后才出版?于是,我回京后也上了孔夫子旧书网,居然搜到1991年一版一印的版本,毫不犹豫地以240元高价买下了装帧简陋、印刷粗糙、定价7.50元的旧书。
2011年9月,我访问圣彼得堡;虽然这是一座俄罗斯历史文化名城,但最让我翘首企待的是拜访老朋友纳博科夫故居。
在圣彼得堡,出了酒店就难得看到或听到英文;由于对俄语一窍不通,真感到自己像个文盲。我手里拿着地图,对着街名,比来比去,寻找纳博科夫故居。又走错了,我对先生说,好像应该在下一个路口左转。(出门时先生总把辨别方向的任务交给我;自然,一旦需要开口问路时,任务就落到他身上了)我刚收起地图,一抬头看到身边暗粉色的建筑物墙上一块方牌;再仔细瞧,居然认出了纳博科夫的英文名字。我大喜,原来并没走错!眼前的楼房正是莫斯卡亚街47号。我感到纳老似乎在同我开玩笑,居然又一次出其不意地出现。
谢天谢地,纳博科夫纪念馆里有人可以讲英文。一位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接待了我们,先给我们放了一段BBC 1962年对纳博科夫的采访。当时的纳博科夫63岁,声音洪亮,神采飘逸。采访录像看完之后,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是他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我永远不会回到那个警察国家,那个指定你读什么书、告诉你如何思想的国家!似曾相识,令我心中隐隐作痛。
走进展览大厅,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台老式打字机,孤零零、黑漆漆地立在一张特大书桌的绿绒台面上。这是纳博科夫的打字机吗?我禁不住问。小伙子回答,这应该是纳博科夫父亲的打字机,他本人是不打字的。我猛然想起,纳博科夫的创作,都是手写的,而且通常是写在卡片上;一本小说往往有几千张卡片。据说他常把卡片洗来洗去,以求发现新视角、新开端和最佳结构。他的作品大多都是妻子薇拉打字成稿。展厅里的玻璃柜中陈列着一本又一本纳博科夫题献给薇拉的作品: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除了写着“献给薇拉”及日期,还有纳博科夫手绘的蝴蝶——或正面、或侧面,或栖绿叶、或落红花,多彩多姿。我在这些已经泛黄的书页面前驻足良久,一一品味纳博科夫连字带画的手迹,和手迹后面蕴含的伟大爱情;身后的打字机似乎响起了噼呖啪啦急促的打字声,我心中顿时又出现了另一对珠联璧合的夫妻:手拿书本,当即口译的杨宪益,和一边飞快打字,一边润色译文的戴乃迭。这样的文化夫妻,他们永恒的爱情,丰富的人生和硕果累累的事业,总让我感动。
离开纳博科夫故居时,先生在前,我随后。在先生正要开门的刹那,他突然叫道,蝴蝶!果然,门玻璃右下角,一只红棕色、黑白斑的蝴蝶在斜射的阳光中拍打着翅膀。我赶紧打开相机,咔哒咔哒地按着快门,生怕蝴蝶飞走。我惊异,这样一座密闭的大房子里,哪里来的蝴蝶?难道是工作人员饲养的吗?本想问一下,会讲英文的小伙子已不见踪影。转念一想,我何必凡事都要探个究竟?看了那么多的蝴蝶标本和纳博科夫手绘的蝴蝶,最后竟有一只活生生的蝴蝶为我们的参观划上一个灵动的句号,多么奇妙啊!莫非是纳博科夫那超越时空的灵魂来接见我吧。
纳博科夫的英文自传,《说吧,记忆》,已在我的床头摆放长达两年。或许是因为生活的脚步太匆忙,心绪不够宁静,我始终没有进入读书状态。在圣彼得堡之行将近的日子,我再次打开《说吧,记忆》,纳博科夫那意象丰富、语言精美、文体华丽的“记忆”开始对我说了——于是,我欣喜地走进了纳博科夫笔下那缅远情深、色彩缤纷的“逝去的王国”。
纳博科夫的文字,真是充满了声、光、色、味觉、触觉,还富含隐喻、象征、幽默,以及对觉知、时空观、失与得、政治流亡、思想自由等种种人生问题的哲学思考。作为读者,我们真得平心静气,开启我们所有的感官,张开我们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地欣赏和理解《说吧,记忆》。
虽然是自传,纳博科夫却摒弃了时间上的线性叙事,而以主题、形象、人物为中心建构故事。每一章都独立成篇。全书的十五章,都分别在《纽约客》、《哈泼杂志》、《大西洋(12.44,-0.08,-0.64%)月刊》等杂志上单独发表过;但各个章节之间,又有着遥相呼应、贯穿全书的意象或主题。纳博科夫曾在他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的文学讲座中告诫大家,一个优秀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因为当我们打开一本书时,我们一句一句、一页一页地阅读,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进作者笔下的世界,不可能像欣赏一幅画一样把整个作品一览无余,可以同时细细品味各个细节和全幅图画。全书的整体“画面”只有读完全书才能初步呈现;而许多细节,往往是初读时被忽略或未能领略其意义的细节,只能在重读时一一进入整体画面,凸显其在全书中不可或缺的意义。《说吧,记忆》正是这样一本值得重读的文学作品。
比如,曾以“母亲的肖像”为题发表于《纽约客》的第二章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在剑桥大学读书的纳博科夫假期回到柏林,他们全家流亡欧洲时的寓所;1922年3月28日,晚上10点左右(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写明日期和时间?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纳博科夫在给母亲朗读勃洛克(1880-1921,俄国诗人和戏剧家)关于意大利的诗篇,母亲织着毛线活,时不时插一句评论。读到诗人把佛罗伦萨比作一朵玲珑娇柔、色泽飘渺的鸢尾花时,母亲说,“是的,是的,佛罗伦萨真的很像一朵色泽飘渺的鸢尾花,多贴切呵!我记得——”这时,电话铃响了。读诗的画面骤然静止在突兀的电话铃声中。下一段便跳到“1923年以后”。
当我们读到第九章时,我们才得知纳博科夫的父亲于1922年在柏林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遇刺。这时,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想起第二章中,被电话铃声骤然打断的母子俩读诗的场景。于是,他或她会恍然大悟,1922年3月28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那晚十点左右响起的电话铃声震碎了母亲的世界。如果我们重温那一段,更会体验到那一刻强大的感情撞击——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再比如,第一章中,有一段纳博科夫回忆幼年意识初步形成时的印象:四岁的纳博科夫,走在乡村庄园维拉的林中小道,左手拉着妈妈,右手拉着爸爸……花园曲径、林中小道是《说吧,记忆》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只是在圣彼得堡阶段,那都是私家园林、乡村庄园的曲径和小道;后来便是欧洲各国的公园、城市小花园中的曲径和小道。正如纳博科夫在第十五章中所言,“那些花园和公园同我们一起踏遍了中欧”。第十五章结束于1940年5月20日,纳博科夫和妻子,还有走在他们中间的6岁的儿子,穿过法国西部圣纳泽尔的最后一个小花园,走向码头……这一画面,无疑会在读者心中唤起第一章里幼年的纳博科夫牵着父母的手走在维拉庄园的林中小道的景象。但此时,维拉庄园、圣彼得堡、俄罗斯祖国、完美的童年、朦胧的初恋、亲爱的父亲母亲都已经不复存在。像潜流一样贯穿全书的失去,流亡主题再一次不动声色地叩击着读者的心扉。同时,全书首尾连接的结构,也巧妙地再现了时间的循环与生命的循环。
一切的丧失,都会带来另一种收获。在最后的一条花园小径的尽头,穿过破败的房屋和晾衣绳上飘舞的彩色内衣,是停靠着“尚普兰号”邮轮的码头,轮船将把他们一家载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自由女神俯瞰的纽约。在那个精英荟萃的国度(二次大战爆发后,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包括爱因斯坦、赫胥黎、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夏克尔等等都逃离欧洲,来到美国),自由民主的国家,纳博科夫将开始他新的人生。失去家园,身无分文,在俄国流亡者圈外尚不知名的纳博科夫,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开始,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卫斯理学院、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授课,讲授包括俄语、斯拉夫文学、英国文学、欧洲文学等一系列课程,并在哈佛博物馆的比较动物学馆兼作研究员达六年之久。所以纳博科夫1940年代的职业生涯常常是集教师、昆虫学家、作家于一身。据说在动物学界,纳博科夫被认为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昆虫学家;在文学界,则是爱好收集蝴蝶的小说家。
由于在卫斯理学院的教职始终是按学年签的短期合同,纳博科夫于1948年接受了康奈尔的教授职位,离开波士顿前往纽约州伊萨卡,因而不得不辞去了深深喜爱的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工作。1950年代末,《洛丽塔》的成功不仅让纳博科夫声名大噪,更给他带来了经济上的独立;在康奈尔执教11年后,纳博科夫于1959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
1959年9月29日,纳博科夫和妻子从纽约乘自由号邮轮前往阔别十九年的欧洲。十九年前几乎身无分文,几乎默默无闻的纳博科夫,现在凯旋而归,甚至邮轮上的图书馆为表示对纳博科夫的敬意专门收藏并展示了许多装帧精美的纳博科夫小说和诗集。轮船上的鸡尾酒会上,纳博科夫总是身陷热心的读者或崇拜者的包围之中。1960年代,纳博科夫和妻子长期居住在日内瓦湖畔的蒙特勒,除了因为那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还为了离在米兰唱歌剧的儿子近一些,以便能经常出席儿子的重要演出。纳博科夫于1977年在瑞士的蒙特勒去世。
纳博科夫在书中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在祖国俄罗斯度过的头20年(1899-1919),流亡英德法的21年(1919-1940)及后来移居美国的20年(本书的最终稿完成于1960年代)。《说吧,记忆》止于他和妻子、儿子即将登上“尚普兰号”邮轮之时。虽然纳博科夫在1960、1970年代的采访中多次表示,想继续写他人生的第三阶段,甚至书名都已经想好,就叫《说下去吧,记忆》,或者《说吧,美国》,但最终未能如愿。这对于喜欢纳博科夫的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说吧,记忆》最让我浮想联翩的是纳博科夫人生的第一阶段,因为他丰富多彩的俄罗斯童年和青少年与我的同一阶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极。纳博科夫自小就受到三种语言的熏陶,英语、法语和俄语;甚至在尚不会读写俄语之前就已经可以读写英文了。十几岁时就已经熟读了各种文学名著,包括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等。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童年提供了他日后成熟的创作所需的一切。
我出生于可与苏维埃俄国媲美的另一个国家,我出生的年代正是山雨欲来的反右运动前夕;反右不仅打倒、流放了一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而且从此封了知识分子的嘴(御用文人除外)。所以我的童年不仅没有英语、法语,就连母语都只能一个腔调,一种观点。记得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英语开始受到重视,但我们的英语课本却逃不出当时流行的革命口号。后来我自己课外学习英语,拜了一位当年上海圣约翰毕业的老教师,用的却是伟大领袖的“老三篇”英译本。纳博科夫十几岁时熟读的各种文学名著我十几岁时尚闻所未闻,但“老三篇”却读得滚瓜烂熟,伟大领袖的小红书可以倒背如流。纳博科夫的童年教育成为他日后创作用之不竭的泉源;我熟读的“老三篇”早已记不得只言片语,倒背如流的毛主席语录也只能记住寥寥数语,比如大会小会往往要集体诵读的开篇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再比如朗朗上口,工整对仗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我受到些许人文教育、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后常常思索的一句语录:为什么可以不顾“敌人”反对或拥护的是什么,可以不问他反对或拥护的理由,就一味地、坚定不移地反着来?只因为我们自己先把对方定义为“敌人”?难道人类没有共性,难道社会没有普世价值?这种教导的逻辑何在?但在这样一个国家,人们是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的。
我20岁时缔造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寿终正寝,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文学的春天,是激动人心的恢复高考……
纳博科夫20岁时随家庭离开了被他称为“警察国家”的苏维埃俄国,流亡欧洲。但那时,俄罗斯的语言、文学、艺术都已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内心,成为他在文学的天空中翱翔的翅膀。我头20年的文学匮乏、精神饥饿,造成了我余生的遗憾和知识的跛足。
当然,我无可抱怨,而且还心存感激。正如纳博科夫所言,虽然命运的突变让他失去了塔玛拉(他16岁时坠入爱河的恋人)、俄罗斯、圣彼得堡、北方的白桦林……但比起更为麻木的命运——平稳、安全、按部就班,50岁时还居住在童年的老房子,清扫阁楼时总会遇到已经发黄的旧课本——回想起来,他无论如何也不想错过命运的突变给他带来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快感。于我来说,改革开放的列车把我从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送进大学校园,我深心感激;改革开放的浪潮把我推向大洋彼岸,一个自由与民主的国度,我更加感激;从曾经立志要“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变成今天游历四方的地球村人,我无限感激。我固然无法改变我知识的跛足,但我毕竟学会了自己走路,学会了自我辨认方向。不怕跛足,就怕驻足;只要我坚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我仍然可以走得很远。
如果说纳博科夫身为政治家、法学家、思想家的父亲以他丰富的藏书以及为纳博科夫精心设计的全面的人文教育给了他超群的智慧与知识,母亲则培养了他极其敏锐的感官,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对生命极致的体验。母亲遵循的一个简单的生活准则是“全心全意地去爱,别的就交给命运”。这是一条多么纯朴、善良、超然,而又普世的准则。我愿把它借来己用。结识纳博科夫,我永远感激!
(【新浪尚文-文化艺术】栏目欢迎相关机构合作邀请,详询010-8224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