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故纸堆里出《天香》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28日 07:42 经济观察网
《长恨歌》的创作和出版,让王安忆逆着那个“金钱时代”的潮流而上,获得了文学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双重关注与赞赏。在一个文学退潮的时代,王安忆三十年来一直在自己的文学海域里“ 兴风作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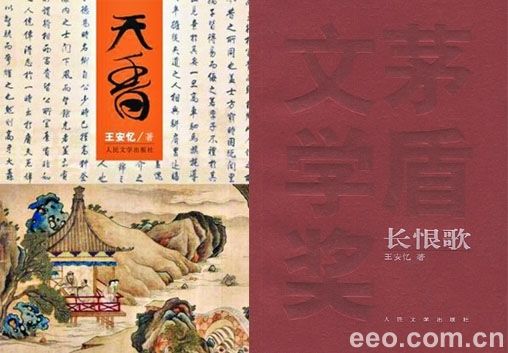 天香
天香1 9 9 3 年王安忆在北京开始了她长篇小说《长恨歌》的创作,这部小说写了两年,1995年出版的时候,同代的大部分作家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高速轮转下被甩了出去,脱离了时代关注的焦点。而《长恨歌》的创作和出版,让王安忆逆着那个“金钱时代”的潮流而上,获得了文学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双重关注与赞赏。
《长恨歌》完成后,王安忆大病了一场。这部26万字的小说,是一场极大的体力和脑力的战役,最终的完成,是《长恨歌》胜利了。而这部作品也更清晰的让王安忆变成了上海的另一个符号,变成了海派评论者眼里张爱玲最有力的继承者。然而与上海的关系,王安忆却明辨, “ 我不是上海人, 我一岁的时候才来上海,我生在南京,祖籍福建。从这点讲,上海滩不是我的故乡,而且我自己也并不喜欢上海,我只是没办法才留下来。对上海的感情,我对这个城市很主观,但也会隔岸观火观察它。对我来讲,我和这个城市之间有种紧张感。”
这种紧张感是1岁时刚去上海的那个小女孩王安忆就存在的,“我的生活——可能跟性格有关系,我的性格是比较孤僻的,或者说就是蛮胆怯的,它使我损失了最早的进入集体的机会——就是进幼儿园。”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王安忆说,每天早上去幼儿园都非常悲惨,后来都变得很阴郁,已经有点儿心理上的问题了,一到那里就哭,非常非常不合群。
这种阴郁的性格伴着她走过了少年,青春期,也度过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苦闷岁月。直到1981年,27岁的王安忆结了婚,她开始了三十年的写作生涯,“生活已经定局,生活和事业都已经找到了归宿。”
回忆起来,王安忆说,在此之前很折腾,人在彷徨和苦闷的时候,往往到情感里边找出路去,情感是没有出路的,这点我很清楚,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写小说,仅仅是结了婚的话,我的婚姻生活也不会幸福的。但是如果光写小说没有婚姻生活也不行,因为写小说太寂寞了,没有婚姻是不行的,这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好命,很好命,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都完成了,就开始好好地写东西,好好地生活。
现在读者谈王安忆必要谈《长恨歌》,这已经使王安忆“百口莫辩”了,她也只能听着,内心里知道其实自己不大有上海本土色彩,这反而也让她对那种所谓的本土色彩敏感,然而王安忆已无真正的故乡,在时代的颠簸下和外界的标签里,王安忆已经属于并代表了上海。
在《长恨歌》之后的15年里,王安忆仍然笔耕不断,女性的韧性,耐力与她自幼性格里的想象力组成了这奇迹的一部分。王安忆说,“小说其实是描写生活的,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对于日常生活有兴趣。男性作家总是写大历史、大史诗,对日常生活的关心,我个人很怀疑。我个人喜欢看女性作家写的小说。”
在王安忆写作的第三十个年头里她写出了《天香》,海派文学里最著名的评论家王德威高度分析并赞赏了这篇小说,他写道:“《天香》意图提供海派精神的原初历史造像,以及上海物质文明二律背反的道理。这两个层面最终必须纳入作者个人的价值体系,成为她纪实与虚构的环节。在她写作出版跨过三十年门槛的时刻,王安忆向三百年前天香园那些一针一线,埋首绣工的女性们致意。她明白写作就像刺绣,就是一门手艺,但最精致的手艺是可以巧夺天工的。从唯物写唯心,从纪实写虚构,王安忆一字一句参详创作的真谛。在这样的劳作中,《天香》在王安忆的小说谱系有了独特意义。”
对话王安忆
问=贝布托 谭旭峰 答=王安忆
问:《天香》讲述的是几百年前的故事,为什么设置这样一个时间障碍?
答:我倒不觉得是障碍。总是不断写新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长恨歌》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它经过了时间,慢慢和读者接近。现在《天香》刚出来,恐怕读者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而且《天香》对于我来讲,不算是历史小说,因为它写的不是历史事件,也不是历史人物。它只是个发生在晚明时候的故事。
问:《天香》既不白话也不文言,怎么定了这样的语言基调?
答:首先,它肯定是白话,但是它确实用了一种没有色彩的语言。它没有地域色彩,不算方言;第二,它也没有现代流行语。我希望把语言推到最本质的面目,因为明代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人怎么说话。我只能做减法,不让新的因素干扰它。方言和流行语都要经过时间、生活、历史的修正,然后才能创造出一种语言。
问: 整本小说语言风格很统一。
答: 对我来说, 写任何一本书,一开始就必须找到最合适的叙述方式,毫不犹豫。
之后,就能进入某种语境。语境对我来讲很重要,是整个故事发生的环境,如果环境没搭好,故事就很难进行下去。所以,语言的方式、风格、腔调,都是一开始就必须找到。小说开头很重要,开头开好,语言定下调子,接下来就很顺利了。
问:据说收集资料的时候,你喜欢去图书馆看老报纸,为什么?
答:我就是不太喜欢在网上查资料,而且我也不上网。如果要查,就请朋友帮忙。在网上查资料,得一个人对着电脑。这会损失很多经验。
问:什么经验?
答: 比如在图书馆查资料,你会在一定的空间碰到一些人,发生一些事情。我特别不喜欢把我的人生经验、人生经历都简略得太干净。而且我不太信赖网上的搜索。比如在《天香》里,某个主人公生在日全食的日子。我请别人查,这个时间一直都没查出来。
理论上来说,在晚明时发生过一次日全食,但当时在任何史书上都没找到,网上也查不到。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位古籍专家,他建议我去查万历年的《本纪》。果然在里面查到了日全食的日子。这使我产生了新的认识——对历史来讲,日全食不是记载在《传》里边,而是记载在皇帝《本纪》里,可见这件事情对皇帝很重要。所以你在查资料的时候如果碰到钉子又找到了解决的路径,这个过程就是你的经验。
我的朋友,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他们用互联网用得很勤奋。但我是一个对机器特别低能的人。
问:写《天香》主要依靠查资料吗?之前你写了很多小说都涉及到上海的各个阶层,这些素材从哪儿搜集?
答:应该说《天香》也不是靠查资料,还是靠故事、靠想象力设计人物关系,推理人物行为。收集素材当然是大问题,因为我的生活比较简单,对于我来说故事总是比较匮乏,紧缺。大部分时候,我处在故事紧缺的状态。
问:怎么碰上写顾绣的故事?
答:顾绣是历史上有的东西,但是写它的难度比较大。我迟迟不敢动笔,觉得很容易写坏。写完后我觉得很满意,甚至超出了我的期望。我自己觉得完成了任务,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
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靠近小说这门艺术
问:《天香》中蕙兰和她的婆婆,你把她们写成一对闺蜜。
答:我不喜欢写太普通的人物性格,我希望能够精彩一点,不一样一些。
另外,情节的需要。蕙兰不仅得用她的女红活养活孤儿寡母,还要传播手艺。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不能改嫁。但我个人倾向认为,蕙兰并不是出于对封建礼教的遵从不改嫁。因为如果是对礼教的遵从,就把蕙兰放低了。
怎样才能让她不改嫁?而且让她承担起对这个家庭的照顾。我想她和她的婆婆应该是一种非常要好的关系,而且彼此间有精神交流。当我写她婆婆的时候,我很注意写她的性格。每一个人我都要给他性格,性格要为以后的情节承担责任。假如我把她的婆婆写得非常软弱,我也会很过瘾,但恰恰相反,婆婆在关键时候都支持蕙兰。
问:但和谐的婆媳关系不常见。
答:我们首先知道,在那个时代里的婆媳关系不像今天。今天的媳妇为什么和婆婆搞不好关系,因为今天的媳妇都有经济独立能力,也要自己的生活。以前的婆媳关系不是这样,以前的媳妇对婆婆很尊崇。但是我又不想写得那么拘泥,我完全不想写一对旧式婆媳关系。我要写这对人物在一起的生活,我要把她们写得有乐趣。当然还有感情上的倾向,至少要让我写的时候有乐趣。我觉得这一对婆媳都是很有趣的人,她们在一起很开心,她们能够沟通,能够交流。这才使蕙兰不改嫁,在家坚持下去。她完全不要做烈女,对她来讲现实就是这样子。她有小孩,要把他拉拨大,还有一个婆婆,她不能丢下婆婆不管,这是做人最最基本的道理。
蕙兰进这个婆家也不容易。她出嫁时,她娘家不能给她备嫁妆就拖延下来了,是婆家不断催,把她催来的。所以,婆婆对媳妇有恩。今天的婆媳关系和那个时代完全不同,那时伦理还很坚固,而伦理背后有背景。
问:《天香》里的这些女性都是几百年前的人物,你怎么和她们交流?
答:你说的问题也是写作当中碰到的一个困难。一开始无从下手,可是后来再一想,人的性格和命运,哪个时代都差不多,只是我们表现的方式、处理方式可能会有些不同,但基本上差不多。想到这一点,心就踏实了。
问:你是否考虑过,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会不会有一些男性作家可能没有的感受?
答:总的来说,我觉得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靠近小说这门艺术。小说其实是描写生活的,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对于日常生活有兴趣。男性作家总是写大历史、大史诗,对日常生活的关心,我个人很怀疑。我个人喜欢看女性作家写的小说。
问:比如?
答:比如最近我就很关心一个印度的,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女作家,茱帕·拉希里。她最近出的一本书叫《不适之地》,写的是一个疾病解说者。这个女作家写得很好。首先,她写的东西很生活。其次,她在日常生活中有洞见。她写的是感情、伦理,可其中有见地、有形势,表现得也好。但是很可惜,我不能看原文,我看的是中译本。她出了不少作品,能看的我都看了。
我和上海之间有种紧张感。
问:你的很多书排列在一起时,人家会说是在给上海这个城市写历史。
答:这是批评家们从我的作品里分析出来的。有时候,诠释也会过度。如果你说我在写历史的话,我可不敢当。至多,我写的历史是个人史,很主观,而这种主观脱离不了自己的经验。如果搞上海史的专家来看,他们会挑出太多的毛病。但小说不同,小说是绝对主观的,它一定是虚构的。我们这些人,做研究缺乏全局观,缺乏归纳能力。所以在小说里,千万不能说
我是在表现历史,这是过度诠释。
问: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的回忆》里有一种忧愁。你一直在写上海,你对上海是什么感情?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对这座城市的情感变过吗?
答:我和上海的关系,恐怕没有像帕慕克和他的故乡那么简单。我不是上海人,我一岁的时候才来上海,我生在南京,祖籍福建。从这点讲,上海滩不是我的故乡,而且我自己也并不喜欢上海,我只是没办法才留下来。对上海的感情,说来说去都没有像帕慕克那么一往情深。我对这个城市很主观,但也会隔岸观火观察它。对我来讲,我和这个城市之间有种紧张感。
问:有人把《天香》跟《红楼梦》作对比,《天香》是在大喜大悲后,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为什么你没写一个悲剧,而是选择了回到庸常。
答:把我的作品和《红楼梦》作对比,我觉得这太高抬我了,就像当时说我像张爱玲一样。但你提到结局的一点恰恰非常有说服力,区别了《天香》和《红楼梦》。
顾绣从民间到贵族阶层后,它又回到民间去,然后遍地开花,整个过程吸引我去写。它并不是大家族败落的故事。大家现在喜欢用“文化”,但是我很不喜欢用“文化” 这个词。我想说的就是个物件,它从民间来,到贵族阶层,经过一番修饰、提高、升华后,它又回到民间。
我重视的是过程,而恰恰这是个过程,决定了我和《红楼梦》绝不是一回事!
问: 《天香》是一个圆形结构,从起点回到终点。
答:这不能说是“回到”,如果说“回到”有点贬低它了。在我看起来,民间是个气场特别大的空间。
问:《天香》问世,正值你的写作生涯30年。有特别意义吗?
答:我就是很自然地在写。不仅是《长恨歌》,《长恨歌》之前我也写过很重要的小说,比如《叔叔的故事》。我认为,一个不断写作的小说家,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有意义。
在《长恨歌》和《天香》之间我写过很多长篇小说,每一个长篇出来后,别人的问题也差不多,都会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比如《长恨歌》之后的第一个长篇《富萍》,批评家对它的评价比较高,甚至觉得它突破了《长恨歌》。所以很难说,一部作品将要在你的写作生涯里占据什么位置,你自己完全不能预测,写到哪儿算哪儿。
最主要的是自己的感觉,《天香》写完后,我心里还是很踏实的。
王安忆年谱
>1954年3月生于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母亲作家茹志鹃,父亲剧作家王啸平,自幼受母亲影响很深。
>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
>1970年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
>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1976年于《江苏文艺》发表处女作散文《向前进》。
>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
>197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平原上》。
>1980年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
>1981年初结婚,丈夫李章,结婚时为徐州某乐团指挥,后调入上海音乐出版社任编辑,曾编辑出版文学传记《孤独与超越———钢琴怪杰古尔德传》。
>1981年,因旺盛的创作欲以及无法忍受坐班时间的禁锢,旷职离开《儿童时代》到徐州写作,完成《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5-1986年《小鲍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6年应邀访美。
>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2000年《长恨歌》获选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