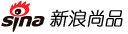方方:无法改变历史 只能不要忘记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20日 07:24 新京报
今天的武汉人,许多都已不知晓北伐战争中那艰苦的40天战役,太多的年轻生命在这些日子里永远消逝,当看到一份逝去的名单时,方方决定把曾经的中篇小说完善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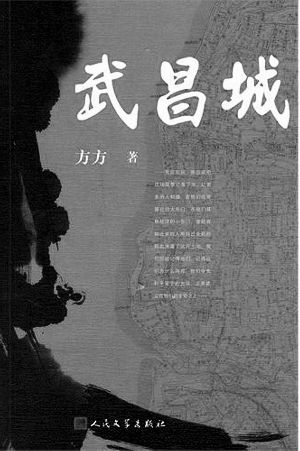 小说《武昌城》叙述的是1927年前后武昌城的一段历史。
小说《武昌城》叙述的是1927年前后武昌城的一段历史。接受采访这天,方方的心情很恶劣,她大学的同学去汉江游泳,结果一去不复返。她整个下午都在江边搜救现场,回家得很晚,尸体没有找到。“一个如此熟悉的朋友,突然就永远消失了。人生有时真很残酷,也很无奈。”她说。不知道如果把这样的情景和她的小说《武昌城》联系在一起是否合适。今天的武汉人,许多都已不知晓北伐战争中那艰苦的40天战役,太多的年轻生命在这些日子里永远消逝,当看到一份逝去的名单时,方方决定把曾经的中篇小说完善起来。许多的生命在80多年前逝去,在方方的笔下,或许他们又再次复活。
“武昌城的围城历史,人们所知有限”
新京报:谈谈你自己和武昌城的渊源?
方方: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武昌区。说来应该算是当年武昌城的远郊。我年轻的时候住在江北的汉口,结婚后就住在江南的武昌。我在武汉生活了五十几年,有一半的时间是住在武昌。一直到现在。
新京报:在《武昌城》的后记里,你写到了第一次知道武昌城存在的讶异感,当你看到武昌城残留下来的一点城墙角,才知道原来武昌是有城的。你还记得那块老城墙砖是什么样子吗?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方方:一小块,砖比通常的大,满有沧桑感,现在应该还在。武昌城以前倒也若有若无听说过,但没有亲眼见过,所以未往心里去,直到看到那些老城砖,心里才咚一下,想到,原来武昌真的有城呀。看到老城砖,的确还是有些震惊,或者说有些激动。伸手去摸它,真的就是想感触一下当年的气息。
新京报:你曾经说问过很多人“知道武昌围城的事情吗?”回答几乎都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们对这段历史了解有限,促成了你起笔写作《武昌城》?
方方:武昌城的历史,的确知道的人不是太多。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了解黄鹤楼时,了解一点武昌城。而对武昌战役即武昌围城历史了解的人就更少。我并不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而去写这部书,而是在阅读武昌战役林林总总的回忆录时,城内城外的事突然引起我的万千感受。人世的残酷和莫测,人生的渺小和无奈,以及战争的无情和可恶,都令我心惊,也令我长想。
新京报:那你是什么契机会去阅读北伐战争的资料?
方方:因为应邀为出版社写《汉口的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的书,大量地查找和阅读了关于武汉历史的资料。相关不相关的内容,我都读。我读的资料,相当部分来自当年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这些资料最重要的部分是当事者的回忆录,其次是代笔者所写的回忆。这项工作起动得很早,有许多五、六十年代就写就的。那时距事件的发生时间较近,很可信。我在写那两本书时,把我觉得可写小说的回忆归类置放,留待以后或许有机会来写小说。几年后,我用这些资料写了《水在时间之下》和《武昌城》两部长篇小说。
“死亡名单促成中篇变长篇”
新京报:《武昌城》最早是中篇小说,你为什么决定扩充成长篇的?你在后记里说是因为二哥的鼓励,但也有说法是因为后来看到了攻城战士的牺牲名单?
方方:的确是我二哥在看到我写的《武昌城》守城篇的小说后,问我怎么不写成长篇。我当即也想,的确可以写成长篇呀。心里便有了这个想法。但攻城和围城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查找更多的资料,才能动笔。正是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份名单。这份名单,比一个死亡人数的数字让人心惊肉跳得多。可能说,是这份名单促使我一定要把这篇小说写成。
新京报:中篇扩充到长篇的一个大变化是增加了攻城篇,这个部分的扩充是怎么完成的?在守城篇后来是否又有变动?
方方:守城篇是2006年写的。我自己很偏爱这篇小说,所以决定写长篇时,到底是扩充此篇还是单列写一部中篇,我也想了一阵。后来还是觉得保持守城篇的原样为好,另外再写一部攻城篇。以两个独立但有相关的中篇组合成一部长篇。同一事件,从两个层面两种角度来反映,也是很有意思的。
新京报:把小说分成攻城和守城,同时每个部分在写作时又以人物为主线交互进行的结构方式是怎么构想的?是否对推动故事情节更有帮助?
方方:最初就是不想再改动“守城篇”,但同时,通过资料也看到,城里和城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局面。所以,如果保留以前的守城篇,而另外写一部独立的中篇完全表现攻城,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两部中篇虽然围绕着同一事件,但彼此都是独立的,它最大的好处,是能让人立体地了解这场战役,了解身处这一灾难中的每个人的心情和命运。
“仿佛我写慢了,会死去更多的战士”
新京报:在小说中,大量的人物死亡,在写到这些人死亡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情绪,是不是自己也会同悲同喜?
方方:那是自然的。我会像读者一样,喜爱我小说中的人物,当他们遇难时,我也非常难过。常常也会有写不下去的感觉。在写夜晚攻城这一段时,有时候在外面办事,朋友挽留吃饭喝茶什么的,我都不肯。跟他们说,我得赶紧回去,我那里攻城正紧张,我得赶紧把这仗打完,回去晚了,死的人会更多。那种状态,就仿佛我写得慢了,会死去更多的战士。
新京报:我知道其实你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中篇的《武昌城》,扩充成长篇后,是否喜爱依旧?
方方:我是很喜欢2006年写的《武昌城》,因我写的时候,觉得自己找到了表达这篇小说的方式。当然,我也是第一次写这样的题材,这需要想象力和推测能力。因为喜爱,所以才没有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扩充,而是将攻城的内容单独写了另一部中篇。这样,一攻一守,我即站在攻城一方,也站在守城一方。各有各的心态,各有各的理念,各有各的曲折,各有各的命运。现在想来,当然还是这样最好。这是我的一次尝试,无论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当然是十分喜爱的。
新京报:不管是攻城的人还是守城的人,其实在人性的部分大家都是相通的。你在小说里面,也一直在充分展现各种不同的人物性情,是否比起单一的死伤数字,这些活生生的个体人物,更能打动你?
方方:那是当然的。数字哪怕多写几位数,它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当你看到立体的人时,那就不一样了。甚至,在我看到一串人名字时,每个名字从你眼前晃过,你都会觉得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从你眼前走过。而这些生命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消失在武昌城下了。想到这些,会有强烈的痛感。
新京报:离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对今天的人你想说些什么?
方方:对于过去,无论多么残酷,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那些事实。今天的人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不要忘记他们。毕竟,是无数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改变中国,使中国有了今天的样子。也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和平安宁的生活。
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