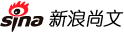消融了二分法的圆明园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2日 09:50 21世纪网
我把圆明园的“明”解释为启蒙,而把“圆”解释为“圆满”和“循环”,因此“圆明园”被我翻译成:人们在其中通过“循环往复地互相启蒙以达到完满觉悟”的花园。
 《萨拉·马哈拉吉读本》
《萨拉·马哈拉吉读本》2000年春夏之交,萨拉·马哈拉吉教授作为11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团队成员,与奥克维·恩维佐等人组团访问杭州、上海、北京。他们的行程被密集的走访、艺术家见面所填满。在杭州时尚有湖畔居从容的茶叙,在上海还访问了艺术家工作室。到了北京,为了节省时间,不得不采取作品集体演示的模式。据说甚至有外地艺术家带着作品资料专程赶赴北京来“看病”,而且不得其门而入。
北京的演示会上,因为人太多,几乎所有的录像作品都是快进着演示的。抽空我给策展人团队介绍了当时“后感性”小组的一些工作。那些激烈地处理身体、身份、死亡议题,混乱而不雅的创作引发了来访者的质疑,而我援引佛教的身体观念和狂禅的创造力激活模式来解释一些令人迷惑的选择。会间休息时,萨拉从访问团的人群中站起,走过来和我交谈。
在杭州喝茶时我就注意到访问团中的这位印度裔学者,他细腻而宁静的眼神总是传递着一种“暂缓下结论”的警觉,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智慧气质。多年后我才完全理解,这种警觉性是一种思维活动对自身的反省能力。它糅合了伟大的欧洲学术自律和深不可测的印度自我觉悟技术。在它的基础上能够生长起一种非暴力而又富于建设性的知识生产的“友谊模式”,不温不火,生机勃勃。
那次交谈的内容我自己几乎忘了,直到读到萨拉为2008年广州三年展所写的文章,看到了那些谈话的痕迹。我们似乎类比了佛教觉悟和艺术活动的能量。我把圆明园的“明”解释为启蒙,而把“圆”解释为“圆满”和“循环”,因此“圆明园”被我翻译成:人们在其中通过“循环往复地互相启蒙以达到完满觉悟”的花园。萨拉注定深爱这种阐释,这和他的眼神中对“友谊模式”的知识共同体的要求一致。
在他的文章中,他进一步把“启蒙”用佛教的本意解释为“点燃心灯”。这不是胡塞尔所误读的亚洲知识模式,不是一种权威性的方法和法理,而是一种“试验性的自我加工精神”。通过自我检查,创造出进入知识共同体时必须具备的警觉的主观状态,这时候我们才拥有一种聆听和回应他者的能力。
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友谊模式,既和胡塞尔描述的希腊广场上争辩的友谊模式相似,又有微妙的差别。胡塞尔的希腊广场上的个人之间,是平等的固执己见者之间的争辩,广场是意见与意见之间进行格斗的舞台。这种思路暗含着妥协性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广场上这些不准备自我检查的意见,最终也许不得不依靠票数来决定胜负。那时,共存只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强制性容忍”。那时,我们便不得不面对民主的最大困难,即更不周全和审慎的意见有可能更符号化,更具有简单粗暴的表演能力,因此获得更多的票数。这时,即使是德勒兹更新过的那种不追求“一致性领域”的友谊模式,似乎也不能防止“头等的平等”的出现。权威和等级,压服和暴力会偷偷地回来,启蒙会倒退,苏格拉底会一再地死去。
而在萨拉的“圆明园”中,“自我”首先是争辩的对象。自我反省的目的是从自我中解脱出来,点燃心灯是为了照亮自我的复杂结构,外在力量甚至是促成这种自我试验和自我启迪的必要元素。
萨拉所阐释的这种亚洲知识模式,并不是欧洲知识模式的对立面,不是简化的对直觉、身体、神秘的赞美而反对欧洲。胡塞尔的失误正是这么对亚洲进行了简化,那只是在纳粹种族主义紧逼之下,重新阐释欧洲精神时矫枉过正所塑造出来的他者。但是,大量的亚洲叙述者的自我阐释其实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前进。依据简单的欧亚二分化,用代数的方式,代入理性/感性、逻辑/直觉、单向/多元等等二分法。再转而把另一选项作为欧洲知识模式的困境的解药,从而得到“东方既白”的结论。
这种简化二元论是深藏在我们很多人思维习惯中的痼疾。甚至在我们和印度学者交流时,也很容易用这种二元论来构造我们的论述。在比照今天的中印社会发展和思想异同时,中国就成了秩序,印度成了无序。换一个场合,我们比照中国和日本时,中国会摇身变成秩序/无序二元论中的后者。再换一个场合,我们把中印日堆在一起命名为亚洲,进入欧亚论述的时候,整个亚洲又变成了无序。最后,当人们比照美国和欧洲时,积重难返的老欧洲又会被阐释为无序的深渊。即使我们注意到无序的深渊是如何营养丰富,我们也已经预先落入了一种思维圈套。
从《萨拉·马哈拉吉读本》的五篇文章中,我们如果不够审慎,也很容易落入这种简化二元论的模式,因此误读萨拉真正的建设性意见。
我把出现在五篇文章中的对立角色列出一个二元对立的列表,这是一个读者容易简化地对立的元素表:
我的列表并不严格和准确,更不是胆敢用如此粗暴的模式,切割萨拉那种佛陀说法般流动的、机锋四出的伟大交谈方式。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操作性的理解尝试。
在每一种分类中,萨拉的身姿都有点略微向后者倾斜。萨拉一直有一种对实践的推崇。崇尚达达主义式的、混乱的解放力量。这和他的优雅谦恭恰成对比。崇尚无知者的力量,这和他的博学恰成对比。在文字中,他一直有论辩的对象,这和他的慈悲无争的个人性格也恰成对比。但萨拉思想的精妙之处,在于每一次他都不是简单地认同于解放叙事。每一次他都不是简单地站在造反者、混乱和无序的创造力的阵营中,为自己的阵营理直气壮地呐喊。而这正是我在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理论家那里经常看到的。那些解放叙述往往充满了夸张和不反思。几乎每一次,萨拉总在提出:别急,现有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有问题,但是造反派的强迫性对立思维会导致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来关注复杂性,让我们暂缓下结论,让我们来看看艺术家的实践产生出了什么。
比如,在关于“用视觉去思想”的建议中,萨拉很小心地提议,要警觉流行的图像理论中文字/图像、话语/视觉的简单二分法。把视觉材料简化为“图像语言”,进而展开关于所谓“读图时代”的叙述,最后导致话语规则越过二者之间切割整齐的边界,成为理解视觉材料的基本模型。而我们要做的是,要让观念即桎梏、视觉即解放的简单对立关系慢慢消失,把形象保持在鲜活的边界上。这才是杜尚式的“延滞”状态。
同理,在翻译问题中,执着于透明的翻译是同一性的幻觉,但在它的另一个极端,过度执着于“不可翻译性”又是种族隔离的悲剧。萨拉想说的甚至也不是简单地站在中线上,因为那也是一种新国际哥特主义,无作为的“混杂性”翻译腔而已。所谓执高明而道中庸,是要“跨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模糊不清和清楚透明的双重运动”,既要重拾混杂性的活力,又要对混杂性重新编码。
又同理,我们既要警惕对于欧洲价值观的普适性表述,要去更小心地理解后殖民理论的历史复杂性、实践和理论不能互相取代的复杂性、策展话语对后殖民理论自身的粗暴简化。也要警惕那种对于欧洲价值观的建设性的无视。要警惕多元文化论述中的“强制性容忍”只不过是一种多元文化管理主义。那里面充满了对于差异性的再现主义谬误,而具有建构意义的差异性恰恰就在这种再现论中迷失了。在策展话语中,这种多元文化管理主义正在成为新的偷懒的来源。因此,我们和后殖民所说的再见,不得不是一种深情的再见。正如费耶阿本德对波普尔的理性主义的再见,是一种深情、恋恋不舍的再出发。
这种谨慎的态度,让萨拉看到了泰戈尔之类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建设性。他们提出的方案并不是简单的造反和颠覆,不是自居于东方的神秘甚至神化落后,而是对自由知识的新大陆上人民生活的重建。那种简单的造反逻辑其实暗中迎合了胡塞尔们简化的亚洲刻板印象。更建设性的方案是杜尚式的“延滞”和汉弥尔顿式的“播散”,是一座活泼的“圆明园”。在那里,我们点亮内心的灯,随时自我试验和改造,循环往复地互相启蒙,和他者成为友谊的共同体。而不是由多元主义的律令所强制,不得不学习容忍他者的存在,并一再地陷入翻译的焦虑。
伟大的智者萨拉启示我们:对立面的双方所站立的正是同一个地面,对立面的双方所站立的正是同一级台阶。而圆明园并不在这里。
(作者:邱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