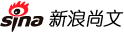我们时代的流言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0日 08:36 新视线
张爱玲在《流言·女人》中评道:男人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人。女人虽也留心相貌,却不失偏颇,同时也看重智慧谈吐风度等项。这大致是对的。记不清是美国作家辛格呢,还是马拉默,写过篇小说,讲一个单身男子,通过介绍人不停地相对象。那介绍人,给他拿来许多照片,有美女,有丑乖的……这边是挑肥拣瘦,然后,抱怨,失望,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我觉得那人很像我。
 张爱玲般的上海风情
张爱玲般的上海风情我们1950年代生的人,因教育不良,恐怕都积了些怪毛病,男女交往都非正常。那时,在女子面前,别说放肆,哪怕只是稍献殷勤,靠拢一点,她们都有可能红着脸嗔骂你“怪物”,或“骚哥”。我们城市是这么骂的。过去骂女人,爱用“骚货”。“骚”呢,就是异性吸引的低俗化,谁能忍受自己是货物呢?大概难于启齿的事,中国人都往死里骂,往货物骂。所以“骚哥”算不错的,至少沾了“哥”字。“怪物”就不同了,跟“骚货”相似,根本没谱谱,一被骂得没了谱谱,也就完蛋了,因为你马上就意识到,你和你追求的人不属同类。于是这代人便常常置异性于幻想,动手动脚,现实里却手脚无措。一个人越是回避着当怪物,就越是本能地拉拉扯扯,便又和道德发生了冲突。
现在,我就拣记得起来的女子说说。儿时,有伙比我大点的院童,在一间堆满稻草的房子里,非让我跟一个小女孩“结婚”,我都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仪式就是把我们推倒在干草里,然后用草盖住。她一个劲擤鼻涕,我受不了,就钻了出来。后来我特别喜欢布鲁盖尔的作品,在他画里,常常出现稻草。他认为,稻草代表着火与情欲,一点就着。就我而言,也不知点了多少岁月,最后才燃的。现在,我相信,一代比一代容易点燃。
后来搬到另一个院子,有两个漂亮的姐妹,我爱上小的一个,因为有次过家家,她蹲在地上,指着自己沾满泥土的黑屁股说,这是大屁股,然后指着前面开裆裤里那个红丹丹(孩子们把彤彤全念成丹丹,如红丹丹的太阳,红丹丹的心)的“M”(当时确实是这么称女性生殖器的)说,这是小屁股,挺先锋的。但我却和大的亲近,因为她块头大,丰满,动辄洗头。她洗头都在院子里,凳上放个盆。这时,我便站在她面前,因为这样可以顺着她斜下的脖子,看到隆在衣服里的乳房。有个美国女诗人,写过这样的句子:“警惕的小乳房”,她一点也不警惕。我是院子里最调皮的,她天经地义地也喜欢我,不管我做什么坏事,比如偷家里粮票卖。有次,我领着帮孩子爬到顶棚上窥视一对夫妻睡觉,结果,踏穿了天花板,不管什么,她都热情地捍卫我,和外面的孩子打架,她也护着我。后来,我当兵去了东北。临行前,我们孩子似地确立了恋爱关系,约好通信。我很想念她。但要知道,我们是雷锋团,雷锋老端着冲锋枪站在松树下,让人肃然起敬,不敢近女色。雷锋好像也相过对象,但为了共产主义,他把个人问题放到今后的日子考虑,结果,幸福尚未来临就牺牲了。直到现在,我仍不明白,他指挥倒车,怎么就让这辆车碰倒的电线杆给砸死了。雷锋没恋爱过,我不忍着点咋行,实在忍不住了,有天下雪,便钻到烂汽车头里给她写信,壮丽的河山,繁荣的祖国,紧张练兵,以防苏修,学习,生活,积极上进,健康……然后,非常严峻地考虑了很久,在结尾处落了个“吻你”,先就自己吓得没感觉了。然后,泥牛入海,没了动静。她大概觉得我很下流,属怪物类,就不理我了。暗自检讨,也确实觉得有些“下流”,因为写“吻你”时,我脑子里的落嘴处,正是我觑了个正着的乳房。吻嘛,就是吻激动人心之处嘛,要不,吻哪里呢?当时又没书本说该如何做,当时的电影,好像也都没接吻嘛。《列宁在十月》里,全喊着“弗拉基米尔·依里奇”,“乌啦!”然后握手,拥抱,黑鸦鸦的人群,鲫鱼似的都在那里唼着枪口和红旗。《清宫秘史》,小李子只晓得“扎”。朝鲜片,除了唱歌跳舞,就是扔苹果。都没吻。
“文革”时,我姐在工人造反兵团的文工团跳舞,我常跟着玩。穿了身洗白的军装,像个“小八路”,哥姐们都喜欢我。那时的人,没那么骚。兜里要揣本红宝书,而且还要一个流派的,才闹恋爱。我姐就和白哥闹恋爱。白哥成分不好,便没闹成,因我爹妈是“革干”,一遇填表,我们总填“革干”。其实,爹的真正成分应该是“地主工商兼资本家”,妈倒真是地道的“贫农”。他们参加革命较早,属地下党,组织派他们接头,“嘭”一声就恋爱了,“嗤”一声三个娃崽,先还是红色,“文革”一到,就成了黑色和狗崽子。
 形形色色的人与时代
形形色色的人与时代在文工团,有人教我拉小提琴,有人教我画水彩画,有人教我跳舞。跳的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双手勒缰,两腿交换着,一弹一跳的,马儿也是想象的。我喜欢上了教我跳舞的一个姐姐,恋爱了嘛就想为她做点什么。有天,我到姐姐们的寝室去,见她床上有些东西,不问青红皂白,抓起来就要去洗,大家全在笑,原来里面有条乳罩,我确实不知女人咋会用那玩艺,出了个大洋相。
后来长大了,说媒的也多了起来。我难得管,谁要让我去见见,我就见见,谁要给我看照片,我就横眉竖眼地挑剔。反正我这辈子和女人没什么缘分,只要不给骂着什么“怪物”啊,“骚哥”啊,“流氓”啊,“瞧你熊样”啊,“白伙食”的就行了。我反击骂“流氓”的办法,就是搬出小说中的“牛虻”,想象着是他。
我妈知我的德行,老说我要找的“只有书里画的”,让我现实点。她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对象是她们地下党领导的女儿,学钢铁业。我还在当兵,人家叫我们“哈尔滨,只知道立正稍息”。那时最时髦的就是背个人造革挎包,我背了,傻啦吧唧的。我问她能否像革命媳妇一样镇守后方?结果,没门。然后是个教授的宝贝女儿,她的近视眼珠好大啊!姐说“近视遗传”,算个理由。居委会也来关心我,拖了个女子来,头眼印象不错,但总觉得哪不对头,一时也说不上,第二回,问题出来了,原来她的骨架过粗,让人觉着任何一个角度都会圪着人。后来是个打羽毛球的,满苗条,可一开口,满嘴龋齿,恍惚她曾有过两排雪白的牙齿,只是后来被当作羽毛球一颗一颗打出去了。有个老诗人的夫人也挺关心我的,先介绍了个研究川戏的,脸膛子跟川戏的“变脸”差不离,手一抹,各种怪脸就变了出来。结果,半途还给金发老外抢走了。据说,我们以为漂亮的,老外觉得丑,我们以为是丑八怪,他们看来却是西施。我常想,如果,弄个丑女移民委员会什么的岂不两全其美。老外得东方美女,华人遍世界,吾国吾民便没那么拥挤抢饭吃了。后来,她又给我介绍个胖女子。其实胖也没什么,俄罗斯妇女哪个不胖,但“卡秋莎”一唱,便倾城倾国。俗话说“胖子养人”,难怪前苏联出了那么多大文豪。问题是,这胖女的父亲是公安局长,像我这么吊儿郎当的人,非党非团,如果犯错给告那么一下,问题可就闹大了。还有次,别人又给我介绍了个女子,说她勤快、孝顺、大方、节俭、模样儿不错,拿得出手。来了,坐在沙发上,抽象的品德一时半时也看不出来,鼻子眼睛也还齐全,但她一个劲用手指在那掏鼻屎,请她吃饭,她还是不懈地掏着。
另一回,是让我去见宾馆搞旅游的。我喜欢旅行,没准弄好了,两口子一块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岂不很美。谁知一见,那毫无轮廓的身材,大头——我的脑袋已够大的了,她的恐怕比我还大。这些都甭提了,但见她,浓妆艳抹,浑身上下没一处不是金光闪闪,银箔熠熠,尤其是那飘飘欲仙的高跟鞋,又黑又亮,七拱八翘,上面还缀满各种怪头怪脑的东西,如果跳贴面舞,不小心踩你一脚的话,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同学的妻子也给我介绍对象,这次说是演员,唱歌的(我眼睛亮了一下),先叙她如何受了些苦,对于受苦者,是要拯救的。但我纳闷,按时下风尚,唱歌的,多为靓女,要么就是一些阴阳不分的人,要辨其阴阳,非摸摸胸脯不可,哪需这般。接着同学妻说,其人上台并不怎么难看,关键是,要看怎么看了,而且,要看是什么样的人看了。于是,我同意看了。一进来,那女子还没让我看清,便掏出一盒磁带塞进音响,放她录的山歌给我们听。那是她唱得很红的一首歌。若只闭眼听那悦耳之声,确实是番享受,恍若跟一个绝色的妙龄女子,骑在一匹马儿上,向蓝天白云、幽幽的山谷漫游。可现实地一看就惨了,我怎忍心形容她呢,我只能说,立在我们几个人中间的简直就是根棍子。从上到下都离不了一个“瘦”字,那细细的两条腿唷,在宽大的裙子里飘荡,让人觉得生活就像没根基似的。
有时,我确实因为没有耐心而失去了根基。我遭遇过多少女子啊!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女子,多年前见到,还风姿绰约,再见,心宽体胖,还孤身一人。你猜她咋说,她说:“我要找一个能给我零花钱的丈夫。”有次,又遇上个自由派女子,你猜她称做爱是什么来着,她说:“此乃小菜一碟。”
钟鸣,1953年生于成都。诗人,随笔作家。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91年出版随笔集《城堡的寓言》。1992年短诗《凤兮》获台湾《联合报》第14届新诗奖。1995年出版随笔集《畜界,人界》,1997年出版随笔集《徒步者随录》,1998年出版三卷本《旁观者》和批评文集《窄门》,2003年出版自选诗集《中国杂技,硬椅子》,2009年出版随笔《涂鸦手记》。现为自由作家。
(作者:钟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