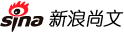也斯谈香港文学往事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06日 15:45 东方早报
也斯即梁秉钧,1948年出生于广东新会,现为香港岭南大学讲座教授。他是诗人、作家也是香港文学研究学者。 在香港,只有也斯其个人的成长、写作经历和香港这座城市六十年的发展如此紧密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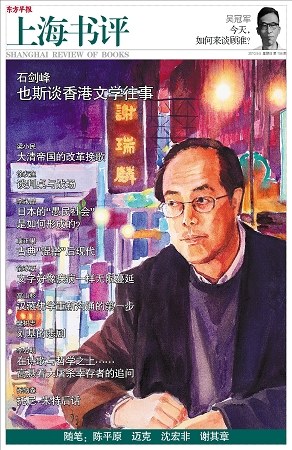
在创作上,也斯的上一部作品是去年出版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在十二个相互关联的故事里,也斯试图在创作上回到香港本土说故事的传统,用欲望感官去触及回归十多年的港人生活;在学术上,梁秉钧花了大量气力去梳理1950年代香港文艺的各个面向,本土的、西方的、杂糅的、传统的等等,都构成包括文学在内香港文艺在1950年代的各个面向,而这样一个传统恰恰在回归前后丢失了。另外一方面,香港从来不是静态的,冷战前哨、反殖民运动、工运暴动、回归焦虑等等,都一次次重塑着港人的精神世界,当然也包括文学思考。
香港文学的源头应该从何说起?1945年还是1949年?
也斯:我最近在做1950年代香港文学的研究,看他们怎么继承传统的东西和吸收西方的各种艺术手法。我首先来谈一下改编的问题,就以我这次在经典3.0上谈的《红梅记》为例。香港有位非常著名的编剧家唐滌,他是广东人,之后到上海学戏,1938年到香港,加入白驹荣的剧团,开始了他的编剧生涯。唐滌生一生当中编了很多的剧,《红梅记》是其中一个。他的写这个剧本的音乐部分时,接受了很多广东音乐,也吸收了西方音乐,他用南音,也用客家筝曲,从京剧和昆曲方面也有得到灵感,还用了一些比较前卫的音响效果,比如萨克斯。除了音乐,他也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戏剧的特色,把西方电影的结构比如分场带入粤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香港在1950年代文艺的特色,电影、现代派文学、武侠小说、岭南画派、话剧、音乐、流行文化等各个方面继承了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的一些不同流派,同时深受西方影响。此外,我们看到1950年代是金庸、梁羽生式武侠小说的兴起,岭南画派从广州发展到香港,一直发展到了抽象的水墨画等等,1950年代以后的香港文艺好象有一个还魂再生的感觉。
香港的文学传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以专栏形式发表在报章上,他们都要写专栏为生,并在这样一个“栏”的限制下做探索。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消失的传统,所以我这几年就从理论上整理这个1950年代。 我在1990年写了小说《布拉格明信片》,那个时候我也做了很多文体、语言上的实验,故意不要故事和人物。但我上一部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故意回到说故事的传统。我回到说故事的传统,也是一种探索和实验,就是在塑造人物、说故事、写人物、写心理活动这个传统之下,是否还有实验的可能。
我更强调的所谓“改编”,改编还是尊重原著,但在此基础上有创意和变化。所以我看文化身份也是这样,不完全本来就有一个很固定的文化身份,也不等于说直接等同于从外面来的移植的东西。文学也是如此。我回到写故事写人物,也可能是回到1950年代的那个传统。我对目前的写作风气有反思,但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还是愿意回到写故事的传统。我也是在改编香港文学传统来对抗所谓后殖民、后现代。
1950年代的香港,其实也处于冷战的最前沿,我们从历史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在香港都有很多动作,在这样一个冷战背景下,香港文学的处境又是如何?
也斯:讲1950年代当然避免不了冷战课题,我们其实可以从1945年开始谈。战后香港其实很有趣,当时最左的理论家在大陆待不下去都到了香港。所以香港当时有非常左的香港和报纸,这造成左的传统在香港一直很强大。一般讲冷战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简化的说法,就是左右对立、壁垒分明。也正因为左右对立,所以很多人想当然认为这样气氛下出来的文学作品都无甚可观。但你也会发觉,这些左右作家在私底下其实有很多交往,他们在报上有笔战,晚上一起打麻将。他们写的很多东西要么反共、要么骂蒋介石,也有很坏的东西,但也有不少很好的作品。而且在那两个很明显政治文化圈外,其实还有很多写香港老百姓、普通人生活的作品。其实,就算是左右也有很相象的地方,我写过一个文章,里面提到一部左派电影《珠江泪》,是左派的那种路子,电影的最后是城市不好回到乡下去;右派也有这样电影,他们调子是,我们回不到故乡,故乡有豺狼。其实这两个电影主角是同一个人扮演的,都用一种地理空间来寄予一种政治理想,思考模式也很像。
当时的香港深受美国新闻处等西方机构的影响,但过去总是很简化说,这是美元文化。但我们看美元文化底下,香港美国新闻处翻译出版的书,其水平都很高,比如乔志高、张爱玲、宋淇等都在里面做翻译,你不能说美国人在香港成立美国新闻处有什么好处,但在底下做的人,对文学是很有看法的,选择这部作品还是那部小说翻译,这更多是从译者个人的文学趣味来定。理论上说,这个阵营是右派的,那么理所当然都是写和翻译右派的作品,其实这种判断太简单了。比如张爱玲翻译《老人与海》是在海明威拿到诺贝尔奖后不久,张爱玲帮新闻处也翻译了很多她不喜欢的作品,这个时候张爱玲他们的翻译与后来余光中的翻译动机很大不同,这里面问题讨论不能用标签去划分。写一个反共小说,可能有作家的政治动机,但也有艺术家个人的艺术探索,所以不能仅仅从意图出发点来看,而是看他们到底写了什么。
我想说的是,怎么在限制里面做最大可能性。当时大家经济条件都不好,稿费不好,这些都是限制,但在这个限制里,我好像看到不同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机会发展和策略,找自己的位置。张爱玲也很辛苦,在香港卖文为生。曹聚仁,右派觉得他是左的,左派认为他是右派,他到死的时候还非常清苦,没赚到什么钱,不太得意。这样的人也不能简单用左右说。
所以,过去把左右阵营讲的太简单了,阵营、意图可能不能讲到反而遮蔽了他们在1950年代文学和艺术创作。
1960年代对于香港来说可能是个动荡的年代,1966年和1967年连续发生了两场大暴动,社会的不安定如何在香港文学本土写作上反应出来?
也斯:1950年代,我们看小说和电影,讲的都是讲移民到了香港怎么生活。到了1960年代,战后出生的一代在那个时候开始成长,整个社会最大问题就是年轻人。上一辈移民觉得好不容易来到香港,很辛苦,重要的是要怎么立足下去,可年轻人感觉到的是社会不公平和贪污,而且对当时的红色中国有一种浪漫想象 。此外,他们的思想资源大部分来自西方,他们也受到了当时西方的学生运动的影响,受到西方嬉皮文化、地下文化和另类文化的影响,我们看到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以及背后的法国新小说。香港年轻人看世界的模式也改变了,这在思想、文化、政治上都有很大冲击。那么1966年暴动,最早是工人罢工,然后是天星码头船票加价,从这些小事后来变成那么大的社会动乱,主要是因为民间不满已经很久了。这个运动后来没有持续下去,是个很可惜的。本来运动来自民间自发的不满,但是左派当时有组织的做了很多事情,最后演变成比较暴力的行为,分水岭是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被左派炸弹炸死了,因为这个电台批评左派的暴力行为。这样,本来民间是比较同情左派的,然后开始分裂,这一事件其实损害了香港的工人运动传统和发展。至此,港英政府有了惨痛教训,所以亡羊补牢,建公屋提供免费教育设立廉政公署等等,民间也有争取中文运动,这都是政府让步于民间抗议。但这个很有组织的工运因为左派而衰落了,到了很久之后才有复苏。
此外,1960年代,香港国族矛盾的爆发,你可以看到民间从来没有站在政府那边,但英国人对香港的兴趣也只有钱,这是跟印度最大的不同,特别是语言教育方面,在印度普遍使用着英文,但在香港除非你要做公务人员和外国公司做工才需要,民间还是使用中文,98%学校教授中文,港英政府对中文不鼓励但也不禁止,对文学也是自生自灭。
这些情况在文学上有反应,当时左派没有很好作品写暴动这类事情,反而是现代派这边,比如马朗有一个小说《太阳下的街》写1957年的暴动;1967年的时候,刘以鬯写了篇小说就叫《动乱》,以现代派技巧来写当时的社会动乱。我觉得文艺对社会的反应,现代派更为尖锐,也没有站在政治、派别的角度来写这些社会现实。后来左派不太光彩,所以没有出来很好的作品写这些事情。所以对当时的社会动荡,一种是像刘以鬯这种用现代派的手法去写,一种是市民的通俗小说,一种是夹杂着方言文言白话夹杂的小说。特别是香港现代派,跟台湾比较,他从来没有排除现实,不认为语言可以自生出很多可能性,香港的现代派因为这个现实环境,没办法孤芳自赏,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这是香港现代主义与台湾大陆不同之处。他们跟上海1940年代穆旦他们的现代派关联更紧密些,但是没有人好好梳理。
“九七回归”对文学不也是一个重要话题?
也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九七回归”冲击其实并不那么大,甚至也搞不清楚香港将来怎么走,有一点迷茫。所以,我想去写系列小说,写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比如我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里,“后殖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时间上的,英国殖民时代终结了,我们现在生活在殖民结束后的时代。另一个含义是解构、破的意思。对香港人来说,殖民时代虽然终结了,但他们依然顶的是那颗殖民时代的脑袋。所以,殖民不仅是英国当年对香港的统治状态,也是香港人本身否定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清楚自己身份的困惑。事实上,在我看来影响香港文学的不是九七回归,而是1995年《苹果日报》的出现,从那之后此类报纸通过减价占有市场,文人报纸刊物纷纷倒闭,文学失去了很多阵地。在此之前《星岛日报》有个青年文艺的副刊,不同青年人在那里发表作品,完成文学事业第一步,只问文学不问出处。现在年轻作家出名很容易,但出名之后很难。他们没有了自发的文学空间,没有人际关系维系一个大的文学社群,所以他们的文字向内,更具试验性。同时,他们在生活经验也比我们匮乏。
之前有一种印象就是,香港年轻人跟政治、社会的距离比较远,反应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他们的作品自我呓语、向内的成分更多一些。可在过去一年,香港年轻人特别是八零后积极地参与到香港各个社会运动,如反高铁,这是否会带来一种文学上可能性?
也斯:这要分两方面讲。香港八零后参与到反高铁等社会运动中,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他们还不满香港地高房价,不满商业公司与政府亲密关系,这些不满都是自发,这本身是个健康现象。以前我们总是说,八零后对现实不感兴趣,其实他们有想法,有意见要表达,但这一系列运动与写作又不一定实际关联。运动本身与写作可能有些影响,也可能根本没影响。社会运动中,八零后表达不满,但写作上需要时间反思,需要长一点时间去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保育、高铁、高房价等这些问题,这种现实写作其实从七、八十年代就有,我想说的是,怎么把这两代写作中好的东西结合起来。比如刘以鬯对动乱的反省,是那么快的诉诸于文字,那个小说《动乱》现在看来还是有深刻反省。 如今,民间的趋向是好的,但媒体是有问题的,比如媒体需要的是更具话题性和轰动性的作品,媒体需求的是什么?如果你要投诗过来,最好那个诗就是直接反高铁的,可这样哪来文艺?不是说,我保护这条街,我就得去写这条街,还是需要跟现实若即若离的感觉。近些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是否意味着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写作者的写作会有以个转向?这还需要时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