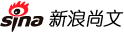黑暗的一幕终于揭开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31日 10:18 东方早报
值得注意的是,纳粹的集中营也好,苏战区的特殊营也罢,不管其中囚犯的身份如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囚犯生活极其艰苦,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苟延残喘于营中。“所以两者的死亡率都同样高,这也是他们两者之间最为著名的共同之处。”

贝廷娜-格莱纳(Bettina Grainer)的《被排除的恐怖》(Verdr?ngter Terror)今年4月在汉堡出版,书的副标题是“苏联在德国设立特殊营的历史”。《世界报》评论说:“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独缺对斯大林恐怖的记忆。苏占区战后在纳粹集中营的原址又建立特殊营,十多万人被关押在特殊营,成千上万的人丧命于特殊营。作者在这部全面描述这一时代的著作里首次揭开了德国战后历史的黑暗的一章。为撰写该书,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她所写下的内容立足于坚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该书现在已成为标杆式的权威著作,贝廷娜-格莱纳对苏占区苏联的特殊营进行了伟大的研究。”
1990年3月,在当年纳粹曾被清理过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又发现了累累白骨,从而揭开德国战后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战后纳粹集中营被揭发被清理之后,苏占区的苏联特工马不停蹄地建立起特殊营。此事在那时的民主德国秘而不宣,成为禁忌,而在西德,却被人忽略和遗忘。从1945至1950年,苏占区曾有十六万人被关押在特殊营。其中有诸如犹斯图斯-德尔布吕克、豪尔斯特-冯-艾因希德尔和乌尔里希-弗莱海尔-冯-赛尔等人,他们都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密谋组织的成员。著名作家瓦尔特-凯姆包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也成了特殊营的“特殊客人”。

从1945年起,苏战区当局便在集中营的原址来个“鹊巢鸠占”,建立起十个特殊营。在里萨的米尔贝尔格特殊营共关押了两万一千名男女,七千人没有挺过关押;在布痕瓦尔德特殊营在押者共有两万八千人,七千人死于非命;在柏林的霍亨勳豪森特殊营两万囚犯中死了三千人;……而在最大的萨克森豪森特殊营,六万关押者中死了一万两千人。特殊营里的条件特殊恶劣,以致被关押的十五万五千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瘐死营中,亦即死了五万五千个男女。
书中强调,一些人之所以被捕和被关押,公开的理由是要进行非纳粹化,其实被捕的人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才是第三帝国的官员和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党)的党员。实际上特殊营成了苏战区当局确保推行蔑视人权的暴虐统治的恐怖工具。人犯的百分之五十都在二十岁以下。
在学校用唇膏画一幅斯大林的肖像,参加有西方倾向的政党,私藏一把锈迹斑斑的手枪,一旦证明你是来自西方的青年,这都会成为给你扣上“共产主义叛徒”,“纳粹的狼人(二战后期在盟军占领的地方纳粹号召组织狼形人妖地下突击队,对盟军进行顽抗。--笔者)”或 “反共特务”的帽子,就会将你逮捕,投入特殊营。一旦陷入斯大林恐怖的漩涡,你就很难全身而退。作者说,很少有人会逃出这种体制的罗网。
评论者克里斯蒂安-哈克认为,格莱纳对这段尚未被人知的历史进行了发掘,进行了开创性的、投入的、示范性的研究,使人恢复了对这些地方所实施恐怖的记忆,可说是建立了功勋。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苏联占领当局逮捕政策的为所欲为的基本模式,其思路完全秉承了当年苏俄和苏联初建时契卡的思路,一切都是策划于密室,以秘密警察进行压制和镇压:“逮捕,拘押,判决,最后是否释放,都取决于安全政策的考虑,具有日常政策的随意性”,也就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决断,因而具有机会主义色彩。贝廷娜-格莱纳指出:“特殊营并非去纳粹化的工具,而是通过专横任意的抓捕,通过恐怖手段来建立共产主义的统治,将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说特殊营乃是为那些威胁到占领当局利益的人准备的。”设置特殊营的目的是将这些“危险分子”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建立货真价实的专制制度。
哈克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曾在其《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写道:大张旗鼓的逮捕会产生一种震慑作用,这足以使得民众噤若寒蝉,振臂一呼的群众领袖也难以产生。”通过恐怖而产生威吓作用,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准则,战后在德国的土地上也得以坚决贯彻。
德国著名的战后史专家鲁兹-尼特哈默曾说,由于明显缺少站得住脚的逮捕理由,所以很多被抓捕的人毫无意义地被空关了多年。占领政策又政出多门,相互抵牾,而这又源于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含混不清,致使被羁押者在1947年的头四个月饿死、累死或被虐待而死者高达一万零五百人。
贝廷娜-格莱纳写道:“那些被判决的人完完全全陷入了苏联的司法之中而不能自拔。因为他们无论是在虚的方面还是在实的方面都和苏占区当局发生了冲突,毋庸置疑,他们也和苏占区所谓的新秩序的建设发生了冲突。他们之所以受到严厉的判决而被投入特殊营,也是出自占领当局安全政策的偏执狂,对德国示以惩戒之意。”
被捕者在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1922-1934,此处应是借用。--笔者)式刑讯逼供室时所供出的是真还是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都亲手在所犯罪行书上签了字。
该书的第二部分调查的是被捕的过程和经历,那种令人有失尊严和令人恐怖的体验。经过逮捕、审讯和判决之后的囚犯可说是精疲力竭,颜面尽失,精神上垮了下来。而在营内折磨他们的花招也是百出。为了便于监管,苏联人将囚犯分为“贵族囚犯”和一般囚犯,这和纳粹集中营的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所谓“营中贵族”,大多是刑事犯罪分子,对其他囚犯为所欲为,大施淫威,极尽折磨之能事。
贝廷娜-格莱纳将特殊营和纳粹的集中营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大于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但与苏联本身的古拉格群岛(苏联劳改营)相比,又可说,何其相似乃尔。为此她得出这样的结论:特殊营乃是苏联本土惩戒体系的一个变种。
值得注意的是,纳粹的集中营也好,苏战区的特殊营也罢,不管其中囚犯的身份如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囚犯生活极其艰苦,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苟延残喘于营中。“所以两者的死亡率都同样高,这也是他们两者之间最为著名的共同之处。”
在苏战区的特殊营中,专横、苦难、恐怖和死亡的历史,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至今还没有适当的位子。尽管有积极的探讨,有个人的回忆,有大量的出版物,可关于特殊营的回忆还是阙如。2006年举办了德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展览的时间相当长,然而民主德国的历史也只是点到为止,受到后母般的对待,特殊营事并没有提起。为什么?贝廷娜-格莱纳猜测,很可能是1953年6月17日事件和1961年8月13日垒砌柏林墙盖过了所有其他的事件。前者是指东柏林工人罢工,人数高达三十万人,最后苏联出动一个装甲师进行弹压。东德建造柏林墙的理由是“防止西德军国主义的突然核袭击”。两次事件,使得许多人死于非命。那时西德当局利用这种政治大气候,火上浇油,千方百计促使有利于西方的发展。不用说这当然是德国历史展览的重中之重,特殊营无暇顾及。
上世纪七十年代,社会民主党执政,总理勃兰特实施东方政策,他访问波兰,华沙一跪,奠定了东西方缓和的局势,这时东西方的话题主要讲缓和,合作,友谊,有鉴于此,西德也不好意思,据贝廷娜-格莱纳,无情揭露斯大林当初所犯下的罪行。不仅如此,为了服务于东西方缓和政策,西德国防部甚至对作家瓦尔特-凯姆包夫斯基刚刚出版的《特殊营的报告》的特刊进行修改。在这份报告里,凯姆包夫斯基描述了他在鲍岑特殊营八年的生活。除了顾及到缓和政策而外,贝廷娜-格莱纳认为,整个的时代精神都不适于揭露斯大林主义的民主德国的不义、恐怖和死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德国发生了反对越战、反对权威、反对传统、反对腐朽过时的教育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反对纳粹的东山再起,呼唤基层民主,要求性解放的学生运动,学生当时所崇拜的英雄是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切-格瓦拉,胡志明和毛泽东。不少学生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肃然起敬,有的学生认为民主德国是“较好的社会主义德国”。在此种情况之下,揭露特殊营之事显然也不合时宜。“那时对纳粹进行进一步的揭露变成了绝好的课题。”
作者抱怨说,在讨论和揭露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摇身一变,东山再起,重又身居要津的同时,往往据此把联邦德国打成法西斯国家,或者说具有法西斯特征的国家。然后梦幻出在西德发生了种种匪夷所思的荒诞之事。有人如若说到特殊营事儿,那就很快被扣上极右保守的帽子,甚至说你和纳粹沆瀣一气。此种情况直到1990年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战后65年,柏林墙倒塌20年,斯大林主义和民主德国专制政权所造成的牺牲和灾难还是没有大白于天下”,这令贝廷娜-格莱纳感到特别的不平。在学校,那些孩子们也对战后在德国土地上建立起像纳粹集中营一样的特殊营的事儿也是闻所未闻, 这很容易造成学童看问题的片面性。作者提出“有意义的、平衡的要求:既要揭露纳粹的罪行,决不美化它,也不使其相对化,也要清算斯大林在德国所实施的恐怖。”
对特殊营的回忆也会激起对德国人所遭受苦难的回忆,这会使人想起战俘营,想起大轰炸,想起大逃亡,想起被驱赶。战后波兰但泽地区,捷克苏台德地区,苏联伏尔加以及罗马尼亚的德裔全都被驱赶至德国,这是德国人至今尚未了断的心结。看样子,有些德国学者要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说起了战俘营,瓦尔特-凯姆包夫斯基说:“有人给我讲起战俘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与其相比,我在鲍岑的八年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在书的最后贝廷娜-格莱纳问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些认为暴力的牺牲品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她自己回答道,对特殊营的历史进行更深入一步的开掘和研究,还要对相关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然后客观地、无情地秉笔直书。评论家哈克说,贝廷娜-格莱纳系统地、全面地、规范地首次揭开了战后德国史黑暗的一章,可说功勋卓著。他建议,她的著作应被被纳入学校的教材。他还建议,该书也纳入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出版计划。
对德国战后史进行梳理,重新探讨,并揭发出原先不为世人所知的事端,从而使人们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这应该是件积极的事儿。但在这里笔者认为应该注意的是,首先分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两者不可一锅煮。在这里我想引证俄国战后第一个获取文学诺奖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话,他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我没有任何理由谴责苏联,。之余我在那里病倒过几次,也曾在那里受伤,那时自然现象,这个自然便是战争。而且我一直很清楚:没有人邀请我们到那里去。战争中炮火是朝人打的。……”他在另一处继续写道:“苏联战俘在德国战俘营中的死亡率高达57.8%,这意味着330万苏联战俘死在德国战俘营;德国战俘在苏联战俘营的死亡率在35.2% 至37.4%之间,这意味着110万至115万德国战俘死在苏联了战俘营。”(《伯尔文论》,袁志英等译,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