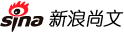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中国通”但非“最后一个”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3日 15:01 东方早报
贾葭先生的《最后一个中国通》(6月13日《上海书评》)一文,显系读罢《李洁明回忆录》的有感而发,其破题之语是:“李洁明去年年底病逝之时,美国外交界曾有人士惊呼,‘最后一个中国通走了’。”美国外交界是哪一位如此“惊呼”?文中未见说明,据我所知,去年11月16日,这位美国前驻华大使因前列腺癌并发症去世四天后,曾有人在港报撰文,题为“美国最后一个中国通死了”,其实并不确切。
对于李洁明(James R. Lilley)的去世,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给予的评价是“我国最好的外交家之一”,他“激励了几代中国通”。 继李洁明之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评论这位前任时,只提到他生长在青岛的经历有助于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毫无任何失去“最后一个中国通”的意思。看来,发出“惊呼”的只是港报上的那篇文章,“语不惊人誓不休”,与美国外交界无甚干系。
李洁明的回忆录,英文书名原意是《中国通:亚洲冒险、间谍与外交生涯九十年》(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倒是完整而透彻地概括了其一生事功,不知台湾的中译本何以弃而不用。综观李氏的全部经历,自称为“中国通”也恰如其分。他从中国回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开始情报工作生涯,就直接或间接地搜集和分析中国各方面信息,又因缘际会地从幕后走到台前,先后出任里根政府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老布什政府的驻中国大使,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华政策的研议和执行。尽管如此,这样的“中国通”在美国大有人在,他决非“最后一个”。
即便不算与李洁明相差整整一代的外交官,如美国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同辈中也曾出使中国的芮效俭,就是依然健在的“中国通”。这位美国赴华传教士之子,于1935年出生在南京,1950年回到美国,大学毕业后考入国务院,相继在曼谷、莫斯科、香港、台北、北京、新加坡和雅加达等地工作,担任过美国驻新加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大使。他涉入中国事务很早,1975年任国务院远东司中蒙处副处长,1978年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经历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成为驻华大使馆副馆长。他通晓中文,能抑扬顿挫地全文背诵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李后主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据说,闭着眼睛听他讲普通话,听不出是出自一个美国人之口。直到现在,七十五岁的芮效俭还不时接受记者访问或参加论坛,就美中关系新进展和新情况发表高见。
贾先生文中提到那位娶了华裔妻子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若论中文能力,他肯定不及李洁明和芮效俭,但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团队成员之一。一个有趣的例证是:洛德戏称自己是“冷战”时期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美国外交官,因为1971年7月9日早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开始秘密访华的“破冰之旅”时,他作为政治助理坐在飞机的最前排。此后,他又随国务卿和总统十度访华,堪称美中关系正常化前后过程的唯一见证者和参与者。至于说对中国文化及国情的了解,有出身世家的夫人包柏漪在侧,洛徳自不亚于李、芮二位,他当年首次来华在宴会上用筷子的本事曾让中方官员吃了一惊。
倘若不是局限于外交界,目下仍然活跃于学术文化界的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夏伟(Orville Schell)和高棣民(Tom Gold)等,都是被美国政府倚为资深智囊的“中国通”。实际上,因为李洁明是从资深情报官“半路出家”,由老布什的政治任命而成为外交官,与国务院系统的职业外交官颇有些区别,由此派生的某种无奈和不爽,他本人在回忆录中数度流露。以美国外交界的现状,不可能因李洁明的病故而有失去“最后一个中国通”之叹,而他事实上亦非足以耸人听闻的“最后一个”。阅读外国政要或名人回忆录,如若囿于一书之得,而当有关的人与事又超出认知范畴,便难免轻信并采用他人的说辞,而人云亦云又自然失之粗疏,很可能以讹传讹,尤其是涉及“最早”、“最后”之类绝对化评语时,往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