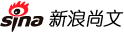阴性阅读 阳性写作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16日 09:34 东方早报
阳性写作之于阴性阅读,正是秉承了两性关系的施受传统。坚硬的鹅毛笔在柔软的纸面上自如挥洒,就是这种隐喻的最直观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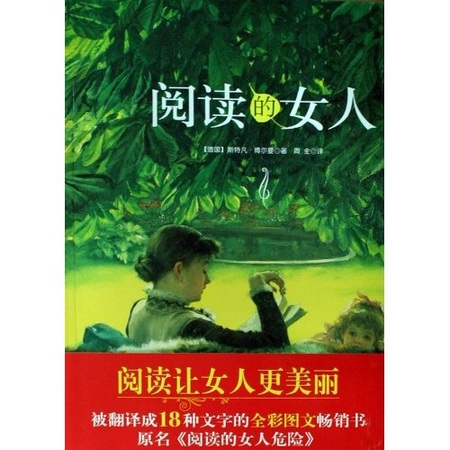
德国人斯特凡-伯尔曼(Stefan Bollmann)编著的通俗图文书,算得上是这类出版物里的常销品种。Women who read are dangerous(Frauen, die lessen,sind gefahrlich),读书的女人很危险。我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此书的英译本封面时,心下凛然——内容先不论,这至少是个耸动的好题目。不知何故,后来再看到它的中译本初版时,书名收干了冷笑、削去了锋芒,成了四平八稳的《阅读的女人》(以下简称《阅读》)。而此书的姐妹篇,Frauen, die schreiben, leben gefahrlich倒是老老实实地译成了“写作的女人危险”。据说,《阅读》一书今年重版时,失落的危险又给编者捡了回来,如此种种,除了归咎于出版社的随心所欲,大概也能做个诛心的猜想:“危险”这种暧昧的字眼,一旦与“女人”这种暧昧的生物勾结起来,难免叫人心生犹疑,举棋不定吧。
虽然畅销,但《阅读》毕竟只是本亲民画册,无论是容量还是深度,都远未达到这个题目可以达到的程度。“读书”之“危险”,其实在人类印刷出版史的头几个章节里,是男女通吃的现象——畅销小说《玫瑰的名字》里那些离奇阴森的故事,不应被仅仅视为艺术夸张。从女权的角度考量,“知识”凌驾于“平民”的特权还得叠加上“男人”凌驾于“女人”的特权才算完整,才能大致解释几百年前,那些手握书本的女性何以总得面对层出不穷的奇谈怪论。《阅读》里摘录了一段德国教育学家卡尔-鲍尔(Karl Cottfried Bauer)发表于1791年的论文《将性冲动引至无害方向之道》,鲍尔大张旗鼓的观点正是当时医学界的共识(其流行程度约等于如今靠绿豆和茄子吃遍天下的“悟本堂”):“……阅读时身体缺乏任何运动,再加上想象力与感受力的剧烈起伏,将导致精神涣散、黏液水肿、肠道胀气及便秘。众所周知,这势必将对两性,尤其是女性的生殖器官造成影响……须知,女流之辈在阅读时,精神及肉体已陷于瘫痪而难以自拔……”替这则“养生秘笈”配的图,当然是那幅著名的《读》(Pierre Antoine Baudouin)。屏风,哈巴狗,斜躺的女人,滑落的书。卢梭曾经针对这种“只用一只手阅读的书籍”发表意见,指出“那女人意乱情迷地躺在椅子上,把右手伸入解开的裙摆下”。
事实上,关于妇女和读书的问题,卢梭发表过的指导性意见还有很多,随手就可以再补上几段:女人应该唱歌,但没必要识谱;女人不应该学数学;女人千万别看天才的书,因为她脑子不堪重负;教育女孩子的目的是为了使她取悦男人,因为女性天生就是“取悦人和被人征服”的;“看官,你更喜欢手里拿着针线的女人呢,还是身边堆满各种小册子、乱写诗歌的女天才呢?”可能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卢梭本人饶有兴致地勾引了一个目不识丁、从未被文字污染的女佣,跟她生了五个孩子,一边写《忏悔录》一边挨个将他们送进育婴堂。类似的论调,康德也津津乐道:“女人不要学几何,学历史时不要在脑袋里装入战争,学地理时也不要有城堡的知识,因为女性有弹药味就跟男性有麝香味一样不好。”
然而,男人训诫的那么多“不要”,恰恰反证了那些神奇的“小册子”,是女人们多么想“要”的东西。随着印刷的普及和小说的勃兴,这种势能日益积聚,必将转化成一股让出版商们无法抗拒的动能。卢梭口中大可以高唱“女子无才便是德”,可他在清点腰包的时候,不会不知道那些“千万不能看天才的书”的女人,为他贡献了多少版税。按照年代推算,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想,Baudouin画上那个被文字勾引出裙底风光的女人,手中滑落的,正是当时风靡闺阁的《新爱洛伊斯》。养在深宅里的女人,一张开手指便漏去大把光阴的女人,注定是小说这种新兴的梦想载体的最狂热的追随者和消费者(我们还有必要列举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吗?)——当大男人们把持的正统知识界还在努力抵御小说的入侵时,沙龙里的女主人非但先一步缴械,而且乐于成为阅读的意见领袖。二十世纪在美国一呼百应的奥普拉读书会,其实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十七世纪的沙龙传统。只不过,当时的沙龙也是社会嘲弄和讪笑的箭靶,出入沙龙的仕女与交际花差不多是同义词,不信你可以去细读莫里哀那本《荒唐的才女》(Les precieuses ridicules),想想这个precieuses到底有几层意思。无论如何,其时,阅读(小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阴性的动词,所以这种行为本身也被越来越浓厚地赋予性别感,进而,安排给风尚画女主角的道具,也越来越频繁地围绕书本做文章。这些图像的顾客群——“修道院的小住持、年轻气盛的律师、体态痴肥的财务官员与其他品位不佳的人物”(狄德罗语),一方面仍然端着假道学的腔调,一方面享受着画面中与书本构成互动的女人所带来的娱乐效果:有了书的存在,画中女人的迷离视线,就有了溢出画外的理由;只要想到那很可能是一本类似于《克拉丽莎》的书信体言情小说,那么,哪怕是那种最专注贞静的神态,也会让观画者觉得与“想入非非”仅有一线之隔。
不过,选入《阅读》一书的画作,大部分都走常规路线,女人与文字的调情往往止于欲盖弥彰之间。路易十五的情妇在布歇的画面中盛装粲然,那本攥在她手里的薄薄卷册(上面的文字都勾勒得清晰可见),更像是绣在她宽大裙摆上的某种装饰;弗郎茨-艾布尔笔下那个凑近书页的少女,沐浴在纯净圣洁的光线之中,如果不是那只轻轻按在胸口的手,观众大概很难联想到这或许是“精神及肉体陷于瘫痪”的前兆;至于那几幅年代靠后的“裸女读书图”(马凯的、瓦拉东的、霍珀的),编者往往强调现代意义上的疏离感,似乎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小说(当然,更可能是一本《第二性》)不再是无往不利的“诲淫”利器,倒更像是诱发性冷感的苦口良药了。显然,对男性而言,这样的“危险”已经失去了美感。
如果眼界足够开阔,而且不用考虑尺度问题,那么,在《阅读》的篮子里,完全有空间再装进一些更好玩也更点题的私房菜。你只要到视觉大师小白的库存里淘一淘,从冰山上凿下一只角,就足够再编一本《阅读》的番外篇。在那些充斥于十九世纪以来的大众通俗读物的插画、版画、藏书票中,有的是女人们“用一只手阅读的书”。无一例外地,碍手碍脚的蓬蓬裙被扔到了画面之外,从而,女人的“另一只手”如何“红掌拨清波”,也与观众坦诚相见。那些显然是通俗言情小说的小册子,与镜子、床榻、黑丝袜、高跟鞋一样,都是赤裸的女人的随身道具。与书本构成对角线关系的,往往是或具象或写意的“阳性本尊”,无限放大书中传达的诱惑。这些画熟练地揣摩着各种需要,轻巧地达成平衡:对于女人的“情欲控”,既是指斥,也是鼓励;对于观画者的窥淫癖,既是讨好,也是奚落。十九世纪末的一枚藏书票(作者是奥地利人Michl Fingesten,s.malz是他的专用签名)上,凹凸有致但面目略显可憎的裸体女人蹲在高处,底下堆着十来部开本各异的书,再底下,是个瘦骨嶙峋、神态暧昧的男人:观其姿势体位,则你说欲仙也可,垂死也可,惊惧也可,深算也可。如果拿这幅画作封面,昭示“读书的女人很危险”,实在要比维托里奥-马泰奥-科尔科的《梦幻》合适得多。掌握知识意味着觊觎权力,意味着要女上位要闹革命——这黑色梦魇般的画面,算不算是性政治的恐怖大片?算不算是男人们既想看又不敢看的《2012》?
在材料的遴选上,《写作的女人危险》(以下简称《写作》)显得比《阅读》更力不从心,基本上只是古往今来知名女作家的肖像集,外加各人不足千字的泛泛小传(尚不及“维基百科”有料),至于如何“危险”、何以“危险”,全都语焉不详。让编著者犯难的,恐怕不仅仅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图像资料大多缺少足够的冲击力,还有一个基本态度的问题。身为女性写作者,斯特凡遗憾地指出:“小说体裁自诞生时起,就与女性阅读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今日,小说的主要阅读人群也仍然是女性……(然而,)女性已经能够决定小说的发展,这一论断对于阅读比写作更贴切。即使十八世纪大多数的小说都是由女作家完成的,但是她们仅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质量并不高。”这显然是个别扭的句子,“数量占优”一说失之轻率,“质量不高”又让作者无从解释,于是话题匆匆转向,直奔他处。我能理解这种不知所措、刻意省略的企图,她希望仅仅凭着女性直觉,就能一步抵达那个让人尴尬的结论:尽管阅读是阴性的,然而,写作——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写作,却始终是一件阳性的事。
《失落的书》的作者斯图尔特-凯利曾在前言里委婉致歉,因为“本书中女作者的书目非常有限”,原因之一就是那些“刻意将女作者排除到体系之外的传统”。好吧,这彬彬有礼的弦外之音真是叫人沮丧啊:并非是女作者的书保存更好、散失更少,而是,女性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太轻太浅。她们那些被湮没的作品,连书目都不曾留下。当然,例外总是有的,但那些短暂而辉煌的时刻常常被解释成历史的偶然。比方说,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成功,是因为彼时的日本男贵族都在忙着学习用汉字表情达意,处在阵痛中的官方语言还无暇顾及口头文学的需求,而宫廷里的妇女仍能自由使用假名记录家长里短,于是,《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的诞生,看上去就像是捡了个胜之不武的便宜。
但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不需要女人顶班的。渐渐地,连女人自己也开始相信,她们的句子是流出而不是吼出的,它们理该是缺乏肌肉力度的,理该是精致而匮乏有效营养成分的,理该是斜体的,理该在突然提高音量时变得刺耳。女性写作者承受的“危险”,不只是制度、阶级、经济、历史之类的抽象概念,不只是比男作家高得多的自杀率,而是所有这些因素和现象合成之后掰碎了弥漫在生活细节里的——它们迫使你在下笔时总在怀疑有没有忠实于自己的声音(我得承认,每次被别人仅凭文字误认为男性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窃喜一番),总在怀疑你的风格是否不够女性化或者太过女性化(喜欢标榜自己的文笔雌雄同体的,总是女人)。伍尔夫在吁求“一个自己的房间”时,试图将所有这些细节都塞进那个象征意味浓厚的“房间”里,好把女作家面对的困境一次性清算。然而,让女权主义者深深沮丧的是,这种秩序化的编排,恰恰是最符合男性思维逻辑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个伍尔夫与写《达洛卫夫人》时的伍尔夫,在语言风格上是有显著差别的——而且,愈到晚年,她就愈是倾向于避开具有所谓女性风格的表达,愈是极端地想动摇两性之间的差别,尽管,写下这些词句时,她就端坐在属于她一个人的房间里。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权主义几乎未到鼎盛就开始走向声嘶力竭、理屈词穷。到最后,该呐喊的都呐喊过了,想论证的论证不了,或许我们可以借来狡猾地抵挡一阵的只有那种玩世不恭的隐喻:阳性写作之于阴性阅读,正是秉承了两性关系的施受传统。坚硬的鹅毛笔在柔软的纸面(在《危险的关系》里,纸更是直接置换成了曼妙的女人的臀部)上自如挥洒,就是这种隐喻的最直观的写照……
时至今日,聪明的女性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文坛偶像是永远不会过时、懂得与游戏规则讲和的简-奥斯丁(美中不足的是,她没能得到一桩伊丽莎白式的婚姻),而不是倒霉的勃朗蒂姐妹或者西尔维娅-普拉斯。在阐述任何主张之前,聪明的女作家都要先找一层保护色,先佯装把自己和女权主义绑在一起,拍在案板上开涮:“说说那个以F开头的词儿吧(它可以是fuck,也可以是feminism)。”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演讲台上说起了绕口令:“如果你既是女性又是作家,如此性别和职业的组合是否自动成为女性主义者,而这又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表示你书里不可以出现任何好男人,尽管你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挖掘到一两个?如果你真的勇敢承认自己是那种用F开头的女人,这种自我分类又该对你的穿着打扮造成何种影响(乔治-桑的礼帽和燕尾服闪过)?就算你不是严格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紧张的评论家是否仍会抨击你是女性主义者,只因为你代表了‘写作的女人’这种可疑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