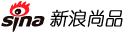马原归来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6月22日 01:36 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
马原的长篇小说《牛鬼蛇神》正式发行,封笔20年之久的他也因此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马原归来
马原归来5月30日,马原(微博)的长篇小说《牛鬼蛇神》正式发行,封笔20年之久的他也因此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整部小说都借用了马原本人的经历作为故事的主线,同时还加入了《零公里处》、《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冈底斯的诱惑》等多部作者20多年前的作品中的段落。也正因为这样,小说几乎囊括了马原在这几十年中所拥有的全部有关神迹的故事。
作者:孙若茜
马原:这个小说的整个经历线是有一点非虚构,与我个人的经历有一点契合,实际上是我在借用自己的经历。但这个经历线没有多大的意义,故事本身的意味是小说的核心,不是经历线。
这也不是一本成长小说,成长小说是不可以虚构的,如果回到小说本身,会看到全部的细节是虚构的,就是进入故事的部分实际是虚构的。我是惯常虚构的小说家,很为自己的虚构能力自豪。
我的成长小说叫《马大哈》,以后会出,其他不是。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很多小说里都会出现作家现实生活的影子,但是在这本小说中,尤其是最后一卷,能明显看出手法特别写实,甚至有点儿像自传体,有没有考虑小说把自己的现实生活暴露得太赤裸了?
马原:这对普通读者来说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关心了作者的状况,而普通读者实际上是不关心作者状况的。所以,这只是一个普通人娶了朋友的女儿当老婆的故事,何必印证作者的老婆也叫“李小花”呢?这件事对读者永远不是问题。
你这个问题含着另一个问题,我的一个朋友也说:“前面三卷写得特别好,最后写得太实了吧?”我这个故事讲的是李老西(李德胜)的故事,故事结尾是不讲李老西了,讲的是他的女儿。后面讲李小花,实际上是讲李德胜故事的方法论。
三联生活周刊:人物大元的经历线和你的经历线几乎完全重合,但是你曾经说人物李德胜更能代表你?
马原:李德胜一定是我希冀的生命样式。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看上去是大元,实际上是李德胜,是大元通过李德胜这个人物去探究人和神,包括人和鬼的关系。我实际上是借大元去代表一个相对日常的视角和立场,借大元去引导读者跟着大元的眼睛去看李德胜的生活。
大元这个角色在整个故事里是探究的角色,对不可知、不能解析的世界的探求,大元提供的角度也是代表了读者的角度。就像我二三十年前的小说情形差不多,所有出现在小说里的人物都不是以独立的人物出现,而是替代读者的视角,让读者从这个人物,这个角色的角度出发走进这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相似的情景,这个故事尤其是。
因为它的主角应该是神鬼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主要是探讨人在不可解析的世界中的位置,人与动、植物相互依存的关系,包括有神的那部分世界和有鬼的那部分世界,所以用惯常的小说方式去看它会有一点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我们经常能在小说中看到大元看待李德胜的仰视视角。
马原:对大元而言,看李德胜是有一点仰视的,李德胜怎么能那么近就穿行鬼界,能够直面神界,跟神对话?李德胜的这种超凡的禀赋是对大元的吸引力所在,对李德胜来说那么简单的事情,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大元是普通人的立场,李德胜是让关心神鬼,关心灵魂,关心虚无和形而上的这部分人群对其形成仰视。所以李德胜当然是作者的楷模,是作者希望看到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故事的整体时间线索特别清晰,但是故事的片段里会有一些时间的错乱感。
马原:因为我一直对时间感兴趣,一直在玩时间的把戏,自得其乐,娱乐读者。我发现讲故事可以从后面讲,但不是倒叙,就是讲后面要发生的事情,明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去讲事情发生之前的事。
因为我始终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就是时间,我在世界上走了一甲子,在这一甲子里,一直关心时间的小说家会有好多独有的心得。我发现时间这个东西是乱的,而乱得没有妨碍,我有时候愿意把时间打乱,把它们混肴起来。因为我这一生中有类似的经验,不是一次两次,是许许多多次,我记得明明是在20年之后,可怎么跑到20年之前去了,你会被自己的记忆迷惑。一生中有那么多事情累积,而你一辈子都在和时间玩着游戏,生命里最好玩儿的就是时间。我特别讨厌那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你的生命就是你的时间,别的都不是你的生命,只有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把完全不同于故事叙述的,像是议论体的文字,完全割裂地放置在每一章最后的0节部分?
马原:我这个是一篇独立的文章《以常识作三论》,我不能称它为论文,但我想它是一篇哲学论辩,没发表,我故意把它分成多段,做成所有的0节部分。目的其实和我原来的小说里面,作者直接对读者说话的作用是一样的,是“间离”。
惯常的小说方式是斯坦尼的方式:尽量把读者拉入角色,跟角色同喜同悲。而我少年开始就特别喜欢布莱希特,他的高明在于知道所有人类无一例外地具有逆反心理:你说这样我一定不这样。所以要“间离”,“间离”在写作上是特别有效的范例,读者时常由于作者的间离,反而对作者更信赖。
我在我的小说中一直用“间离”,20年前、30年前都有大量的“间离”,在这个回合里,我把原来的间离手法换用了另一个方式,是打断。打断的时候就让读者从故事里走出来了,出来以后再重新导入,这并不真的妨碍读者的阅读,如果读者对你的书有兴趣,他还是会把整个书的阅读完成。
而在中间的间歇中,每一次0节出现的时候,就造成了西绪弗斯下山的时空,这个时空,对阅读这本书是至关重要的。在每一次切断的时候,留出了一个时空让读者除了读这段议论文字以外,同时也能从故事里面走开一下,去品一品味道。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分议论虽然是一篇独立的文章,但有时又和小说中的故事联结在一起,甚至觉得就是在依着上面的故事谈。
马原:因为这两万多字的议论先于小说完成,写小说之前我把这段文字作为小说的主旨。
我这个论辩的基本方法论是问题的提出。提出的方面特别宽泛,涉及科学历史、技术历史和人文历史,主要是以问题提出的方式去面对绝对,面对形而上,或者都可以说是面对虚无。
用我的话说,小说的主旨还是探讨人、神、鬼之间的关系,人在宇宙之间的位置。因为有了这个主旨,所以这个小说里的好多内容又似乎和论辩文字是有机的。因为核心是三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仍然没有结论,只是讨论。
三联生活周刊:几年前生病,甚至几乎面对死亡的过程让你放大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马原:实际上这些年都在考虑这个,我的小说一直不太关心爱恨情仇,吃喝拉撒。我一生都在关心绝对,形而上。我的故事都是形而上,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更明确,不讲人间的冷暖的故事。我喜欢在一个特别结结实实的结构里面能做出力量,带出大叙事的气象,我的东西一直没有电视剧、电影,和老百姓期待的东西不一样。
其实在生活里我是一个特别宅的人,每天要去菜市场买菜,在家里做饭、扫地、洗碗,其他写小说的人还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这一辈子我只关心这个小说里关心的问题:动物、植物、神……这也正是为什么这本书里面会有很多原来小说的片段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你会有两部长篇小说面世?
马原:对,实际上不可能一下写两部。一部是要新写的,另一部是已经写好的一个电视剧剧本,是那种门槛低的一个很好看的故事,彻底虚构的一个原创的唐代故事,现在有60多万字。本来打算电视剧出来再写成小说,但是现在决定不等了。所以我要做的是把现有的60多万字的对话变成30多万字的叙述,不需要很长时间,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是不一定马上出,我做事都是兴之所至,想写的时候再写。
但我知道这将是一部我这辈子里特别重要的作品,就像米开朗琪罗说的那样:“大卫不是我雕出来的,他原本就在那个石头里,我要做的只是把他找出来。”我的感受很像这句话,我要做的就是把历史的灰尘拿掉,让它显现出来,它已经在那儿了,我第一次觉得它不是我的,是天的。
(【新浪尚文-文化艺术】栏目欢迎相关机构合作邀请,详询010-8224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