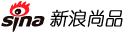“牛鬼蛇神”再扛“先锋”大旗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6月10日 08:41 大洋网-广州日报 微博
蛰伏20年后马原新作《牛鬼蛇神》震撼出版,他是否在经历了文学与人生的双重蝶变之后,最终已改变了自己的观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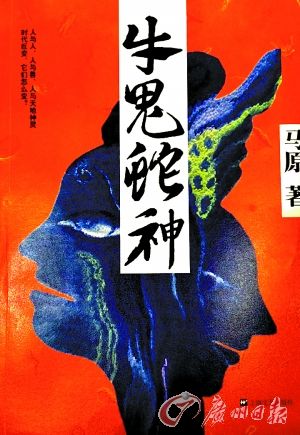 “牛鬼蛇神”再扛“先锋”大旗
“牛鬼蛇神”再扛“先锋”大旗蛰伏20年后马原(微博)新作《牛鬼蛇神》震撼出版 接受本报专访:
近日,记者获悉,先锋派标志性人物马原的新作《牛鬼蛇神》已经出版。本月底,当年“先锋派”五虎将将悉数出现在该书的全国首发式上,为马原“复活助阵”。这或将成为文坛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马原以“叙述圈套”开创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与余华、苏童、洪峰(微博)、格非(微博)并称为先锋文学“五虎将”。他为何在最辉煌的时刻从文学界抽身远去?他的归来,是否意味着先锋文学的归来?他是否在经历了文学与人生的双重蝶变之后,最终已改变了自己的观感?他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20年后回归文学,面临生死很多事情都看透。”
文、图 本报记者 吴波
“20年后,我马原还是一条好汉!”
“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先锋派作家马原独特的语言曾经感动过一个时代。他以《冈底斯的诱惑》蜚声文坛,其《西海无帆船》、《虚构》、《上下都很平坦》等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回避的作品。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上世纪90年代初马原悲怆地宣告封笔。
对于江郎才尽的20年里,马原不止一次害怕。他很绝望,想自杀。
马原已经太多年没有出版小说了,曾经的中国先锋派文学代表作家马原“小说家”的身份也渐渐被人们淡忘。可今年中国文坛最具戏剧性的事情,莫过于抛出“小说已死”论的作家马原竟然携重磅作品《牛鬼蛇神》“满血”复活了!马原用他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记者:“经历生死考验,倍感人生沧桑,20年后,我马原还是一条好汉!”
20年后,马原卷土重来。记者从各方的评论了解到,《牛鬼蛇神》好评如潮。有评论指出,本次马原的复出,跟汪曾祺有得一比,就像汪曾祺那样“回来”的小说家。马原告诉记者,“你别叫我作家,我是一个小说家,现在的作家几乎跟‘砖家’一样,成了骂人的代名词。”他指出,作家的概念变得宽泛了,“我不了解你所说的韩寒(微博)、郭敬明等写的书为什么那么畅销,这些年,几乎能发表字的人都是作家,作家的职业荣誉感早就消失殆尽了。”
“遍观文学史,走了许多年又回来的人凤毛麟角。” 汪曾祺是极少数停顿了二三十年小说创作之后又重新回来写作的前辈。马原说:“我和汪老关系特别好,我一想起他,心里就特别温暖,我还有个伴儿。”
《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讲述了两个男人的故事,大元和李老西。1966年9月,13岁的沈阳红小兵大元小学刚毕业,听二姐描述在北京串联受到伟大领袖接见的场景后,他瞒着家里人搭上一列南去列车。在北京,大元碰上了17岁海南山民李老西,半年之久的大串联运动,把这两个男孩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后来,大元回拉萨,李老西回海南。许多年后,社会变迁,大元忙忙碌碌早已不再写小说,也渐渐想不起自己海南岛上的老朋友。偶然之间,他来到海口,意外与80后的退役女运动员阿花相遇,然后相知相恋结婚。婚礼上,大元才看到,自己的老丈人正是李老西。
当老师、拍电影、做房地产
远离辉煌的20年
1953年,马原出生在锦州一个铁路员工家庭。他说,“在遇见小说前的几十年,干过农民、渔民、汽车装卸工、铆工、筛河石的力工、钳工、整备工、泥瓦工。”1985年,他写了《冈底斯的诱惑》,两年后,与女作家皮皮结婚。
马原认为,写小说是离上帝最近的工种之一,但也是苦差,等同于进窄门。所以这20年,他走出了这道窄门,作为小说家的马原从文坛“死亡”。
后来,他到上海,在同济大学做老师,此外,马原拍了一部纪录片,取名《中国作家梦》。本着对文学的热爱,他本想趁着当事人大都还在,把这些人聚拢到一起,应该就是一部完整的“新时期文学断代史”。十七个月几近两万公里跋涉,采访了120位作家,拍了4000多分钟的素材带,最后剪辑成720分钟,分成24集。他投入了近百万,但纪录片完成后,由于观众不关心文学,目前仍然被马原“金屋藏娇”。
后来,他还拍电影,以自己的小说《死亡的诗意》为主,几个小说的元素糅合在一起。那是2004年,他得了糖尿病。电影没拍完,投资人跑了,后来就不了了之。半成品也被马原雪藏在家里。与小说无关的日子,马原甚至还干过房地产,如果坚持下去,他说也许现在你采访的是“开发商马原”。
虽然中止了小说的创作,但马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学的思考。在他眼里,优秀文学作品分几个层次,依次为深入浅出、浅入浅出、深入深出,至于故弄玄虚的“浅入深出”,基本就不入流了。与此同时,马原还对近些年的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现在的文学评论家们批评的眼界越来越窄,存有重大抱残守缺的问题。比如余华的《兄弟》,在传统阅读出现问题、新的阅读方式没有出现之前,成功地获得了大批读者,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批评界看不到这一点,反而以畅销为由头进行了批评。
对话马原:
回归文坛是对格非的回应
广州日报:《牛鬼蛇神》在文学期刊刚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能给我们的读者谈谈创作这本书的缘起吗?
马原:我回来了,又重新恢复了写小说的能力,让我特别开心。对于现在的读者而言,我只是一个新人。
创作这本书的缘起,是海南文联主席韩少功一直在搞海南长篇小说大奖赛,2010年年底,他向我发出了召唤,当然我最后没有得到他的大奖,我是一个与获奖无缘的人,虽然我是很多大奖的评委。
这还跟我的朋友作家格非有关。4年前,我患上了肺部肿瘤,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3年前,我和格非在北京见面,他对我说,你要是再写小说,你的小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生病了会让你看到比原来大得多的世界。
格非的话一直深藏于内心,我这次写作也算是对那次聊天的回应。
广州日报:选择“牛鬼蛇神”这个题材,是不是20年来一直在积累这样的素材?
马原:《牛鬼蛇神》动笔于2011年年初,当初并不顺利,两度拿笔,两度搁笔,但是到了第三回合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状态。那种激动,那种热情,让我自己都惊讶。写《牛鬼蛇神》的状态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小说的状态是完全一样的,激动不已,手舞足蹈。最终,30万字用10个月就完成了。
其实,写这本书的灵感和老子有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说这段话时,没有说比3更大的数字,所以在我的小说章节也没有看到比3更大的数字,最终,无论哪段故事都归于零。而我意在通过归零这种方式,和老子所说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形成一种巧妙暗合。
为写不出小说而大哭
广州日报:为什么20年不写小说?
马原:这与我离开西藏有关。去西藏使我成了一个写小说的马原,西藏使我脱胎换骨;离开西藏后原来的马原也就不见了,原来的那种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灵感也随之而去。回到东北老家后我才深切觉悟到:离开西藏是我一生中走错的最大一步。
离开西藏好像使我的一切都乱了套,我的婚姻随着也出现了裂缝,回到老家不久,我就与既是夫妻,又是同行、还是师生的妻子离婚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写小说,更确切地说,是没写成一部完整的小说。有时我不服气,想重新证明一下自己的余勇,写了几篇东西,但每一次证明都使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陷入困境,那情形很像自杀前的海明威,拼了老命挣扎。那种苦恼,就差用头去撞墙了。四十岁时,我大哭了一场,因为我发现自己真不会写小说了,或者说写什么自己都不满意了。
希望能写畅销书
广州日报:您会继续写下去吗?您曾说最想写的是畅销书,为什么?
马原:我会坚持下去的,我同时还在写一本古代题材的《玉央》。我突然感觉我犹如圣灵附体,我又可以写小说,所以会一直写下去。
关于畅销书这个问题,这个想法是在拍电视剧时萌生的,现在越来越强烈。在40岁之前,我更看重自己的文学创作对历史的影响,看重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40岁之后,我更看重能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我并不喜欢金庸、琼瑶的作品,但我特别惊异他们的作品在汉语世界竟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我希望写出同样为大众喜闻乐见、但又绝对属于我自己的作品。我要为大众服务,但我的大众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民,而是文学意义上的人民,我想通过为这种人民写作而达到为历史写作的目的。我余生的写作,只为我的人民。
(【新浪尚文-文化艺术】栏目欢迎相关机构合作邀请,详询010-8224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