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短篇小说集《野菩萨》最近在大陆出版,她在北京马不停蹄做讲座,接受采访,和作家对谈,话题却异常集中而分明:马来西亚华文、她有着三重叙事结构的繁复长篇《告别的年代》和新短篇、她的暗黑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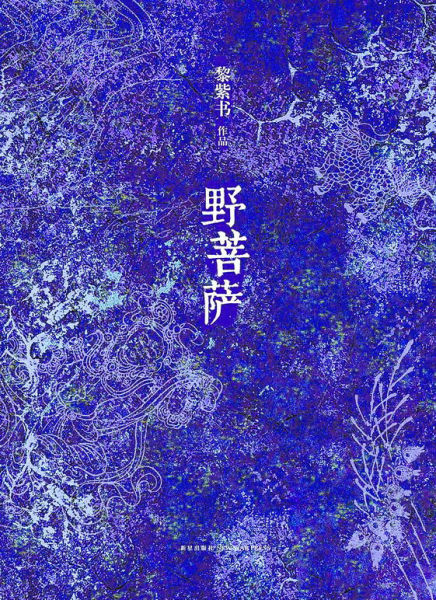 《野菩萨》
《野菩萨》这也自然——对于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用华语写作的作家,人们欲探寻的究竟,其实很容易会被归纳为:汉语在一个马华作家那里抵达何处,它如何被使用和丰富;这样一个频频拿奖的女作家究竟有怎样的人生、写作和对世界的理解。
马华写作 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想象
任何一个进入他国的外来作家,都难以摆脱被以“异国情调”所打量的命运。她的作品在大陆很多人看来,符合他们对于亚热带岛国的想象,她的文字有一种潮湿感,是那种空气中的湿气,甚至包括那种凝滞不散后的霉味。
 黎紫书
黎紫书上世纪六十年代,马来西亚政局躁动不安,并导致一九六七年以排华为诉求的“五一三”事件,之后,华人地位大受打击,华语、华校等沦为被压抑的对象。
作为生于七十年代初的写作者,黎紫书常会被局外人当做观察这样一种国族大义后续影响的样本,这使得她在进入国外华人视野中,常会遭遇被过度阐释的危险。她的第一个长篇《告别的年代》,内涉那段历史,但在她看来,这些旧事被提起,是因为那是父辈一代的时空元素,是人物生活过的背景。
在她看来,她之前的很多马华作家,像年长些的李永平、温瑞安等人,作品中有着对于神州的向往和辐射,但到她这一代,马华人已经很清晰地认知到马华人有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很多人试图拉开距离,写和中国大陆以及港台完全迥异的作品。对她来说,她完全没有这样的企图,她很少着眼大历史写作,刻意靠近或者逃离,她更着迷于个体的存在状态。
暗黑童年 “我对这个世界早有成见”
考察一个作家的童年,往往可以窥见她灵魂潜伏期的形状。对黎紫书来说,这段时期尤为惊心动魄,她在童年经历的失望和恐惧,使得她很早失去天真,那种疼痛,使得她好像为了维护自己童年的权利,躲进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中。
她说:在我的认知里,世界本就歪歪扭扭,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美好、流畅与圆满,其实只是被道德与恐惧这两面哈哈镜合力映照出来的、畸形的影像。
她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身世,父亲有三个家庭,她的母亲是二房。她的成长中,父亲是一个一周回来一次的赌徒,经常深夜回来,早晨又出门,所以这一生,她和父亲的对话不超过一百句。
她的很多作品里,父亲都是缺席的角色。在《野菩萨》收纳的短篇小说《疾》《无雨的乡镇·独角戏》中,她写到了主人公和父亲之间的那种空洞,她也记得:自己曾和父亲坐在同一部车上,靠得非常近,却没有一句话。那个时候,已是父亲病重的晚期,她非常希望那个洞可以填补,却因为太深,而无能为力。
童年经验构建起了她对人性和世界的初始认知,很多年后,她成为一个社会新闻记者,社会新闻巩固着她对人性灰暗的认知。她说,她从不对人性报以厚望,总是做好了失望的准备,而好笑的是,事实让她一次次得逞。
多重视角 小说家是最世故的诗人
天真的丧失使得她很早对人性有所洞察。她擅长从一个现象堆积的事件中轻松找到背后隐藏的逻辑。《卢雅的意志世界》,讲述了她小学的一个经验,就是面对母亲的打骂时,她逐渐开始不哭闹,因为她通过母亲的行为看到了她的焦虑和恐惧,打骂不过是母亲极端情绪的出口,而非自己的过失。
后来,她开始写作,在察觉受到瞩目最好的途径是参加文学比赛后,她像过去准备考试一样,研究获奖作品的路子,拿捏评委的看法,口味,结果一路拿奖。包括她决定最后一次参赛,同时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和时报文学奖,也是她精心研究评审心理后,写作了两篇风格完全不同的文章,脱颖而出的。
她认为,小说家就是最世故的诗人,世故,才懂得世界、人,才老练,才能让人物的性格带出小说的情节,让故事讲下去,同时小说家又是诗人,要文字好看。
她宿命主义倾向的哲学使得她认为自己写作时,对于题材并没有多少选择能力,她总是不自知的被一些所吸引,甚至重复吸引。《野菩萨》收录了她十三篇故事。这些故事抽离出来的元素,就是她不断重复的写作冲动,包括:久雨。阁楼。镜子。梦。父亲。旅馆。寻觅与遗失。她的作品里,镜子是一个让她迷恋的意象。她觉得里边有一个她无法进入的相对的世界。她在作品里设置了很多双胞胎形象,处理的就是这种迷思:看似相同,实则大不同的世界。同时,她喜欢使用第二人称,因为它是第一人称的对照,也是镜子意象的一种投射。这种形式感的迷恋,也被放到她的第一个长篇《告别的年代》中。书中有三重叙述,从而制造了阅读难度。
在第一重叙述中,她讲述了主人公杜丽安的人生遭际,她遇到的爱和幻灭,处理的是她父辈一代的故事。第二重则是“你”的故事,来完成对“杜丽安”这个人的追寻,这是最像作者本身处境的一个人,第三重则完全跳出小说本身和故事本身,讲作者和评论者的关系。在讲述作者和评论者的关系时,她放进去了自己对于那些经常需要另辟蹊径,切入阅读的评论者的一种态度:评论者往往是最孤独的读者,甚至比作者更要孤独。
【对话黎紫书】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野菩萨”作为整个短篇小说集的名字?
黎紫书:《野菩萨》这个短篇是我先有名字后写成的小说。它的很多元素和《告别的年代》相似,是我同样以我的家乡怡保为背景写的一篇小说。里边我同样使用了双胞胎的处理,这是我对镜子意象的一种迷恋。里边的妹妹特别美好,良善,却是残缺的,甚至她的存在最后也是被怀疑的。她就像在一个野地上,一尊被遗忘的菩萨像一样。这篇小说是我后期写的新短篇,也是把类似题材处理得最成熟的,所以拿来作整个短篇集的名字。
新京报:你的作品里充满暗黑元素,可能很多人会期待作者能和生活有所和解。
黎紫书:很多人看作品会期待一个答案,会问为什么不给出出口,但是,我想文学是不负担这样的责任的,我把一些问题,现象写出来,我不能提供解答。我没有给出光明,是因为我看到的真实人性不是这个样子的,我选择做一个坦诚的作者。
当然,作者的作品和他在世界中的角色和位置有关联。像我喜欢的卡佛,一直潦倒,在写作《大教堂》时,他表现出一些愿意和解、积极,这和他的生存状态好转有关。作品和作者当时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是有关系的,也会变化。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