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阅读与任何现实没有关涉,就算你读了再多的圣贤书,它们对你的人生又该有何精神指引呢?
每年的阅读盘点都会让我产生一种无力的焦虑感。不是因为每年的阅读太少,恰恰相反,是因为阅读太多,反而觉得无用。前几天跟熟悉的编辑聊天,他提到说近期的稿子要有一个转变,开始强调书评的实用性。当时的我就忍不住反驳,阅读本身就不该具有实用性,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强调非功利心的阅读吗?但是等面对自己一年的阅读总结时,突然发现,如果你的阅读与任何现实没有关涉,就算你读了再多的圣贤书,它们对你的人生又该有何精神指引呢。
 《沉疴遍地》
《沉疴遍地》某种程度上,我们阅读是为了解答自己内心的困惑,而自己的困惑往往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有关。2010年去世的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他的著作《沉疴遍地》(新星出版社2012年3月版)的序言就是一份“给困惑者的指南”。他指出了现如今我们生活的方式中有着一种根本性的谬误,就是不断地追逐利益:我们知道很多东西的价格,但是从不追问价值几何。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恐惧的时代,不是因为某些恐怖主义的袭击,而是那种对生活中无法控制的变化速度越来越感到恐惧,对无法掌控和重塑自己的生活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我们时代的病症中唯一能够达致的共识。
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危机感,我们的生活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阅读的焦虑其实与这种深深的无力感有着很深的关联。也许是我们想从阅读中找到某种共识的存在感,找到某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是为了逃避现实的焦虑。我甚至可以感觉到自己一年的阅读都是为了回应这种时代的焦虑感。收录在《现代危机》(新星出版社2012年5月版)中的列奥·斯特劳斯的文章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告诫:“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一种思想在一方面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在另一方面的退步为代价。……总的来说,没有真正的进步,只有从一种限制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变。”
历史的进步往往以其他方面的丧失为代价。比如我们的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确实到了人类数千年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在此之外,我们有何进步呢。反而危机丛生,腐败蔓延,贫富加剧,专横的依然专横,堕落的依然堕落,迷失的依然迷失,挣扎的依然挣扎。艾柯在他的专栏集《倒退的年代》(漓江出版社2012年5月版)也表达出了类似的忧虑,看似进步的时代,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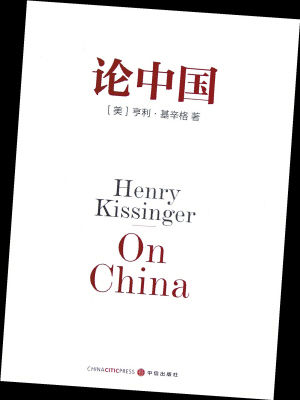 《论中国》
《论中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版)中,借用哲学家康德的话说,人类想要以永久和平,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于人类的洞察力,另外一种是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人类别无选择。也许,现如今我们时代的危机已经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了。很多人都在寻找这种危机的病因,也有人试图在自我理解的范围内开出一剂良药。比如托尼·朱特就力图融合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优势,呼吁我们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
但是,这种想法与他即将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思虑二十一世纪》中表达的观点产生了矛盾,他在那本书中认为,导致本世纪日益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是:过度的经济自由。而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哲学家,我们可能面临这种处境: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想象更美好的世界,而是相反,要思考如何防止出现更坏的世界”。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印度的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中也提到说,面对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腐败与不义,正义问题所需要的是关注实际的生活,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而非寻找绝对的公正;允许不同的正义缘由,而不是允许一种正义缘由而存在。
换句话说,我们从传统中,从历史中寻找危机的解决之道,而不是从建构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理论;最不济也要从已经发生的现实中总结某种经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福山今年出版了他的力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与他之前的任何一本著作一样,清晰而有力。他对历史的观察可谓洞若观火,对政治起源的追溯,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探究我们时代危机的病源所在。
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他的观察与分析都显得过于冷酷。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中,他赞同一种负责任的威权政府,这种提法与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如出一辙,即一种“市场导向的极权主义”,因为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按照他的说法,其最适合的体制并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专制政治的混合体制。这就不难明白,为何他钟情于中国的这种威权性质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一位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一个一直以自由民主为追求目标的西方学者,会有这样大的变化。给人的印象,似乎西方的危机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有种病急乱投医的意味,需要向东方寻求解救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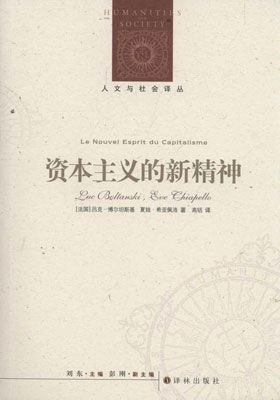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当然,关注这种危机的有不同层面,法国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夏娃-希亚佩罗合著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译林出版社2012年3月版),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梳理和批判,追根溯源,从源头中找寻一种导致这种危机发生的原因。他们一方面想描绘一幅发生变化更易理解的图景,另外一方面是想用这个图式来说明这些年我们对资本主义解释上的缺陷。这种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重新追溯,与福山对政治秩序起源的追溯,可以看作是异曲同工。但是福山的分析似乎更具有宏观的视野,他力图完成康德的疑问,想从世界普遍意义上完成这种人类历史的全部归宿。这种分析占据了历史的优势,却失去了历史的人情味。似乎政治哲学家眼中根本没有具体的个人,只有那些放眼望去的数字与黑格尔笔下的历史的主人与奴隶,我们陷入何种的苦难,他并不关心。
当然这样评价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不正确的,至少他们之间也不尽相同。我敬佩福山的分析,但是更为亲近伯林的多元主义历史观。而在《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8月版),我们又领略到了这位哲学家更为私人的才华横溢的一个侧面。在伯林的所有思想史著作中都有一种洋溢生动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某种程度上源自他生活的丰富多彩。这样具有多个侧面,有血有肉的哲学家是我们所喜欢的。
伯林对俄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有一个偶然的因素,受到了二战的影响。这样的历史的偶然性,让我们意识到历史也不可避免会具有某种特殊的属性,绝非理性解释如此简单。而金雁的《倒转“红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对俄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溯,与伯林的思想史研究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当然,金雁的书写更具有现实的意义,我们熟知中国与俄国之间纠缠不清的历史渊源。对另一个具有历史同源性,而且在二十世纪历史上有着很多惊人类似发展的两个国家而言,这种相互的参照是不言而喻的:对历史的研究往往都是指向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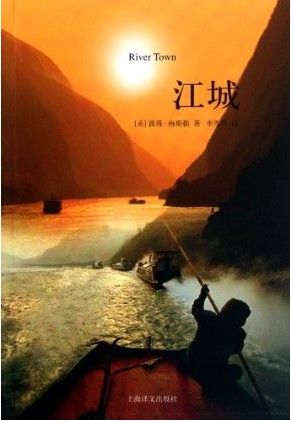 《江城》
《江城》除了对大历史的关注,当然也免不了小现实的体验。今年的阅读中有两本书不得不推荐:一本是何伟的《江城》(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月版),还有一本是加拿大的记者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月版)。前者取材于何伟在四川涪陵的教学经历,后者取材于桑德斯多年游历于世界各地的贫民窟的观察。这是两本充满了感性与深思,融合了历史与具体现实的作品。
贝淡宁在《城市的精神》(重庆出版社2012年11月版)中也有过同样的忧虑,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全球,人类正在经历高度的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城市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漂泊和乡愁成为人类共同的命运,越来越多的人或主动或被动选择在城市落脚。但是如何认识一个城市,如在城市成就自己的美好生活?他走遍了全球的九大代表性城市,力图从中找寻这个孤独的人群如何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但是从何伟与桑德斯的观察来看,他们所呈现的世界才是那个可触可感的世界,而不是历史学家毫无感情的理性分析。尤其桑德斯对“落脚城市”的观察,他从中看到了一个城市发展中那个隐藏在城市背后隐秘的动力,并且对城市的管理者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但是与桑德斯充满希望的建议不同,我所在的城市管理者已经开始清除他们眼中的“毒瘤”,城中村也罢,贫民窟也罢,他们所带给城市的是活力和希望,但是他们所承受的却是无尽羞辱与绝望。
当然,这不是我们时代危机,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