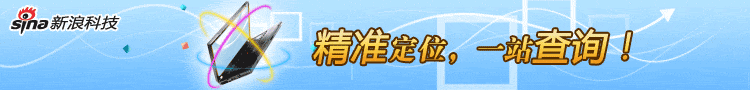散打冠军之死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11日 07:47 中国新闻周刊 微博
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商业格斗赛事背后,层次不一的商业格斗赛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冠军离世的背后,“中国式”散打比赛的魅影危机隐约显现。
本刊记者/马多思(发自海南海口、山西晋城、河南郑州)
 上官鹏飞(右)打中江苏队选手蒋正辉。当日,上官鹏飞代表河南队参加首届CKA 中国武术散打超级联赛75 公斤级的比赛。 图/ 新华
上官鹏飞(右)打中江苏队选手蒋正辉。当日,上官鹏飞代表河南队参加首届CKA 中国武术散打超级联赛75 公斤级的比赛。 图/ 新华2011年12月17日,天气阴沉,山西省阳城县岩山村村民上官西龙经过自家玉米地地头一处新坟时,忍不住蹲在墓前哭了起来。
墓地的主人叫上官鹏飞,上官西龙的儿子,2009中国武术散打联赛75公斤级冠军,2011年12月12日,在昏迷了42天之后,终因伤重不治去世,年仅23岁。
在儿子的坟前,上官西龙一边哭一边含混不清地叫着“飞飞”(上官鹏飞的小名)。47天前,飞飞离家前往海口参加中国武术散打功夫王争霸赛,此后再没能活着回来。
厄运
10月的最后一天,在海口举办的中国武术散打功夫王争霸赛即将开始半决赛,来自河南省散打队的上官鹏飞将要在当晚出场。
出生于1988年的上官鹏飞身高超过1米84,眉清目秀,2009中国武术散打联赛75公斤级冠军,2010年国际武术搏击王争霸赛季军,是河南散打界的“希望之星”。
当天上午7点多,他先后给远在山西的父母和在郑州的女友王诗吟打了电话。上官鹏飞的弟弟上官云飞记得,哥哥留给家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聊了,我马上要出发了”。
“他跟我说他晚上打比赛,打完了给我电话。让我好好吃饭,多喝水,照顾好自己。”女友王诗吟说,比赛之前,飞飞曾在电话中告诉她,这次80公斤级的对手都是国内前四名,个个实力非凡,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10月31日,海口,晚上10点40分,比赛开始,对手是来自前卫队的浑身肌肉突起力气过人的崔飞。
崔飞果然像上官鹏飞预料的那样实力非凡。比赛的第一回合,上官鹏飞在几轮猛攻后便处于下风。第二回合开始刚刚一分钟,上官鹏飞头部先是挨了崔飞一记摆拳,随后崔飞又两次出拳,第二记右摆拳兜到了上官鹏飞的后脑,飞飞顿时失去知觉瘫倒在地。
彼时,王诗吟正在网上看比赛的回放镜头,看到上官鹏飞轰然倒地,王诗吟赶紧拨飞飞的电话,却始终没有人接。哆哆嗦嗦拨到夜里十二点多,电话终于接通了,接电话的是上官鹏飞的队友。队友告诉王诗吟说飞飞没事,说完便匆匆挂了电话。
王诗吟不敢睡,披着衣服坐在床上。凌晨一点多,飞飞的弟弟从山西打来电话:“姐,你帮我爸妈订下机票,他们要去海口。教练打电话让过去护理。”王诗吟隐隐觉得情况不妙,一宿没睡,第二天下午便和上官鹏飞的父母赶到了海口。
4000元比赛奖金
距离昏迷的儿子只有几米远了,但是上官鹏飞的父母只能透过重症监护室的小窗看一看躺在床上的飞飞。其实,就在被击倒的瞬间,飞飞已经极度接近了死亡。河南省体育局的官员透露,上官鹏飞在被击倒后失去知觉,当时呼吸与心跳都已停止。经过海口市人民医院近一个小时的抢救,终于将上官鹏飞从死神手中暂时抢回。11月3日,医生告诉上官鹏飞的家人,由于病人脑部受到的伤害非常严重,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医生可能过于乐观了,11月26日以来,上官鹏飞的呼吸减弱,11月28日出现呼吸时有时无的情况,需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更严重的是,他的主要脏器开始衰竭。12月12日上午,上官鹏飞在深度昏迷中去世。
“重症监护室不允许亲属陪护,飞飞死亡时没有亲人在身边,寿衣也是护工们帮着穿的。”王诗吟说。
12月13日,告别仪式在海口市殡仪馆举行,上官鹏飞的妈妈上官小书紧紧抱着上官鹏飞的尸体不放,几位地方体育局和河南散打队的领导在一旁劝解。这是母亲和儿子最后的拥抱——从上官鹏飞12岁离家习武,每当他回家,上官小书再心疼,也只是安静地看着儿子,和他聊聊天。
在上官小书的记忆里,2011年初那段时间,儿子每次训练结束总说感觉很累。上官小书劝他不要练了,休息一段时间,但他说不行,为了家庭,为了以后能给女朋友幸福,为了自己能有好的成绩,他必须坚持。
上官鹏飞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武术散打是一项枯燥无味的体育运动,只有不断练下去才会有光明的希望,哪怕在以后人生途中很多坎坷路,哪怕再多的困难,也要坚强、顽强地走下去。
河南散打名将张开印记得这位师弟性格特别外向,总在开玩笑。王诗吟和上官鹏飞恋爱后不久就发现,他很幽默。“逛个超市都能把售货员聊得哈哈大笑。”
在弟弟上官云飞眼里,个子高挑的哥哥却是个爱伤感的人,比赛前一个月,上官鹏飞在郑州专门给他过了一回生日,“那天,哥哥拍着我说,你身体太瘦弱了,说着说着他自己就哭了起来”。
上官西龙家只有10亩地,种的玉米和小麦勉强够一家人吃饭。12岁时,喜爱少林功夫的上官鹏飞孤身一人到河南焦作投靠开武校的亲戚学武,大一些后被登封塔沟武校发现并招收。为了给儿子交学武的费用,上官西龙每年农闲都要到附近的煤矿做些苦力活,但是家里还是欠下了近两万元外债。
12月14日,上官鹏飞的骨灰被家人接回了老家——阳城县岩山村。他的遗物,除了几身衣服和鞋,还有一张19000元的存折。捏着儿子的存折,父亲上官西龙潸然泪下,“一般正式队员每个月连工资带补助大约4000元,飞飞是2009年入队的集训队员的,收入只有普通队员的一半,但他却坚持一直攒钱。”
与足球等队员不同,虽然经常参加比赛,但上官鹏飞收入很低。在中国,商业格斗比赛大体分成两类:一类是国家武术管理中心挂名主办的商业赛,此次上官鹏飞参加的中国武术散打功夫王争霸赛便属于此类,这种比赛每年数量不多,奖金也不高。一位知情者介绍,即使上官鹏飞在这次比赛中战胜对手,他获得奖金也只有4000元。
非官办的民间商业比赛虽然数量多,奖金也较高,但上官鹏飞参加不了,按武管中心规定,凡是在武管中心注册的散打运动员不能够参加此类比赛,此类比赛参赛者都是退役选手和业余拳手。
质疑
从上官鹏飞10月31日住院,直到他去世,公众对散打运动本身和裁判、赛前体检、现场医学监督、运动员的赔偿与保险等诸多方面质疑不断。
事发后,许多武术迷第一反应还将矛头指向上官鹏飞当时的对手崔飞,称他“犯规击打后脑”,另外裁判对比赛制止得也不够及时。对此,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小军表示,“当晚比赛后,我们召集了裁判委员会的成员复查了录像,通过反复观看,认定当场比赛使用技术符合要求,裁判判罚得当,没有失误。在搏击项目的对抗中,一方运动员在俯身躲避对手的重击时经常会导致对手的拳套擦到后脑,这在比赛中属于正常情况,并不能因此判定对方运动员是故意击打后脑。”
有评论甚至将上官鹏飞的死归结到运动本身“太危险”,“要说体育运动的危险性,散打运动一定名列前茅”。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小军不认可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武术散打30多年来的首例,突如其来,纯属偶然。”
事实上,在体育项目的危险性排名上,职业拳击仅排在25位左右,排在前面的体育项目有滑雪、登山、攀岩、跳伞、橄榄球、赛车、自行车、赛马等。曾经获得全国散打亚军的戴双海觉得,散打的危险性与职业拳击相比,又小了很多。“散打可以用踢和摔的技术,不像职业拳击那样一味地击打头部。职业拳击的风险都排名在20多位,那么散打的风险性肯定会更靠后。”
“比运动本身更重要的是运动员的安全保障”,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赛前体检和运动员保险是散打运动两大软肋。
上官鹏飞的父亲上官西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官受伤住院后,医生曾告诉他发现上官鹏飞有乙肝,有乙肝的运动员是不能参赛的。
但上官鹏飞却通过了赛前的体检。著名散打选手、上官鹏飞的队友张开印透露,国内赛前只查心电图、脑电图。
相比之下,国际一些格斗赛事赛前体检则比较严格,被誉为“中国UFC(国际顶级格斗赛事)第一人”的张铁泉对此深有体会,“UFC的赛前检查一般有10余项,心、肺、脑电图、验尿、抽血,甚至包括眼睛都要检查。到了临上场之前还要测量一次血压。”
“我们每次比赛前,所有中外选手都要去进行艾滋病和乙肝的抽血检查。”商业格斗赛事“英雄榜”组织者安迪说,“格斗就难免出现伤口和出血,如果其中有一名运动员有艾滋病或乙肝,另一名运动员就很容易被传染上。”
国内几乎没有保险机构愿意给散打运动员上保险。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主任副主任王玉龙说,“散打这样的高危风险项目,商业保险很难。现在运动员上的都是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的保险。”王玉龙表示,“国内比赛像这种出现死亡,最高赔付一般是30万。”
安迪说,他每次都在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给“英雄榜”参赛运动员每人上两份保险。“想多上,但是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规定每人只能上两份。在美国,每名选手可以上高达百万美元以上的保险。”
冠军的结局
“天堂人,元旦快乐!”2012年的第一天,王诗吟在自己的微博中给天堂中的上官鹏飞发去了这样的问候。她和上官鹏飞原本打算今年订婚,然后攒钱明年结婚,但这一切化为泡影。
河南省武管中心主任赵俊透露,上官鹏飞的赔偿还有工伤赔偿以及抚恤金通过一些人性化的协商“已经达成了比较满意的补偿条件”。
上官西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抚恤金在上官鹏飞火化前就到账了,具体数额他不想透露。河南武管中心的人最近还通知他,工伤赔偿和保险正在办理。上官西龙了解到,儿子工伤赔偿的总额将近20万。
上官鹏飞的去世之后,中国散打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武管中心主任高小军去年11月30日说,武管中心今年在散打规则和裁判法上均做了修改,并在总局标准化委员会的指导下制定了标准化手册,已上报体育总局。
上官鹏飞的去世,甚至让国内格斗界变得紧张,圈内人士甚至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就是怕媒体的误解,怕国内因此限制甚至禁止散打和格斗比赛的开展。”大型格斗赛事“紫禁之巅”组织者刘小红说。
现实或许并不像刘小红想象的那么糟。2011年12月17日,2011中泰功夫对抗赛在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开打。这是上官鹏飞去世后国内首场搏击赛事。与此同时,重庆、通辽也分别有终极自由格斗赛和河南电视台的“武林风”比赛同时打响。一天之内三场赛事,分别由广东省体育局、国家武管中心和河南省体育局主办。
刘小红说,上官鹏飞的死给行业敲响了警钟,但不能因噎废食,“这时候,理性与理智比什么都重要。” ★
商业格斗赛的前世今生
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商业格斗赛事背后,层次不一的商业格斗赛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本刊记者/马多思
2011年12月10日晚,国内规模最大的商业格斗赛事之一,“紫禁之巅”武术搏击大擂台第十期大赛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落下帷幕。
“紫禁之巅”由刘小红女士创办于2011年7月,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最年轻的一项商业格斗赛事。
区别于传统武术,现代商业格斗更具对抗和观赏性。而自2000年,中国内地开始了自己的第一项商业格斗赛事——“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12年来,散打王、武林风、英雄榜、紫禁之巅、锐武等商业格斗比赛层出不穷。为了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和观赏性,各种比赛规则“大胆改革”,但是,以追逐金钱为目的的比赛,安全保护令人担忧。
“散打王”诞生
刘小红记得,上述赛事在2000年至2003年间火爆一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散打高手。除了以“柳腿劈挂”闻名的柳海龙之外,还有轻松击败普京保镖的“燕都神影”薛凤强,再加上“白眉大侠”苑玉宝、“草原骄子”宝力高等,种种江湖味十足的名号,使原本不为人熟知的散打选手,仿佛一时有了金庸武侠小说中“盖世神功”。
上述“散打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北京国武公司和湖南电视台三方合力打造,实力很强。“除武管中心外,湖南卫视是中国最好的电视台之一,国武公司也很了得,投资国武的股东中,就有当时大名鼎鼎的德隆。”刘小红说,活动一开始就声势夺人。
2000年初,“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在北京亚运村散打馆正式开赛。与以往任何散打比赛不同,它借鉴国外搏击类赛事的成功经验,对赛事进行了综艺节目般的娱乐化包装——散打比赛引进了总导演、现场主持、灯光、音响、舞美概念,甚至用明星包装的手法包装运动员,这些新奇的手段大大增强了比赛的欣赏性和娱乐性,吸引了大量观众。
在娱乐节目相对缺乏的时代,这个每周播出的散打赛事节目迅速掀起了中国散打竞赛市场化的第一波高潮。2002年,其项目销售收入达到了1300多万元。
但好景不长, 2003年,正准备“收回成本,全面盈利”的国武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突然改组,投资商派来了新领导,提出新的战略和运营模式,加上湖南电视台也退出了赛事转播,原本成功的赛事走向衰落。“当年德隆系崩塌是压垮‘散打王’ 的最后一根稻草,连大股东都被抓了,赛事能不垮?”刘小红说。“散打王”于2004年停办,运作方北京国武公司也随即解散。
水土不服的“英雄榜”
“散打王”倒下后,综合格斗大赛开始在国内出现。
2005年,美籍华人安迪在国内创办了“英雄榜”综合格斗大赛。
综合格斗,又称综合武术赛,英文名叫Mixed Martial Arts,简称MMA比赛。与以往单纯的散打比赛不同,MMA比赛允许各种格斗技巧参与,无论泰拳、散打、空手道、拳击、跆拳道、截拳道或是巴西柔术、柔道、桑搏、摔跤等均可参加。
在美国学了多年柔术的安迪1998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开了个一个巴西柔术班,靠教柔术糊口。2004年,安迪的父母和弟弟从美国来到中国,家人们觉得安迪靠办班教学没有出路。次年,由安迪的父母出资数十万美元,帮助安迪创办了“英雄榜”综合格斗大赛,虽然规则灵活,但比赛却叫好不叫座,2006年3月,当第三届“英雄榜”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之后,安迪的钱已亏得差不多了。他知道,凭自己家人的力量,这无疑将是最后一场比赛。
安迪想起有钱的老朋友——一位疯狂热爱柔术的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纳哈扬。安迪飞到阿布扎比找到了穆罕默德·纳哈扬,肯求他的资金支持。将安迪电脑中储存的英雄榜赛事资料全部看完之后,纳哈扬答应第一年投给安迪80万美元,比赛办好以后还会增加投资。
2007年年初到2009年年底,有了钱的安迪又举办了十多场综合格斗商业格斗赛。让安迪感到奇怪的,这么精彩的比赛,除了门票卖得还算说得过去,竟然没有电视台愿意找他们谈转播的事情,甚至免费提供给电视台转播都没人买账。
此时已经开始尝试涉足拳击商业赛的刘小红和安迪成为好友。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英雄榜”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内容虽然精彩,却不适合中国观众。“在美国比赛中运动员倒地后对手可以骑在他身上继续击打,甚至可以踢倒地者的头;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的观点是同情弱者,讲究点到为止,怎么能够在对手倒地后继续打呢!”
2006年,中央台对“英雄榜”比赛进行了一次录播,虽收视率不错,但终因上述争议最终停播。
“这么精彩的节目,电视台还让我们花钱播出,要是在美国,是电视台花钱。”安迪感到不解。为了维持较高关注度,他不得不出资在要价相对便宜内蒙古卫视进行了几个月的录播,但收益并不如意。看不到赢利希望的穆罕默德·纳哈扬,2010年没有再给安迪投资,“英雄榜”比赛也从此停办。
安全隐忧
在擂台上比功夫,挣的全是血汗钱,而散打选手的收入到底有多高?一位圈内人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现在的商业比赛,选手收入跟赞助费有关。“有的赞助费高,比赛奖金就有上百万,比如广州曾举办的散打比赛就以百万奖金作噱头,冠军到手就有近百万的收入。”但他同时表示,一般的比赛,选手收入不会有这么高,出场费仅一万元左右,如果获得相应级别的冠军,出场费会增加一倍多点。
与选手的收入甚微不同,“散打王”和“英雄榜”的先后倒下并没有阻挡住商家主办商业格斗赛事的热情。继“英雄榜”之后,中国大陆接连出现了武林风、英雄传说、武林传奇、紫禁之巅、锐武等大型商业格斗比赛。“有些县城,甚至一些煤老板个人,都在出资办赛事。”刘小红说,如同玩票一样,很多人有点钱就想玩一把。
各种赛事频频出现,“昙花一现”的也越来越多。刘小红说,很多比赛只办了一届就再也见不踪影。曾推广过中国拳王争霸赛、全国拳击锦标赛等的刘小红认为,赛事必须要有自己播出的平台,而且要符合中国的特点,否则光靠门票肯定存活不多久。
据业界一位评论人士统计,不算国内选手之间的比赛,2011年仅各种类型的中外对抗赛超过20场,接近2006年到2010年国内5年举办商业赛事的总和。
上述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市场火爆,但在场上安全控制却普遍存在盲点。例如,为了迎合观众,主办方在选手安排上更愿意给中国拳手安排一些相对较弱的外国对手,此举人为增加了比赛的安全隐患。此外部分选手的技术也不规范。“其实早在上官鹏飞受伤之前,就有多名国外搏击选手后脑被打,例如2009年中泰对抗中,中国选手击倒泰国拳王蓝桑坤的扣杀式摆拳,同样打中了后脑。”
裁判水平也被认为国内商业格斗比赛中安全隐患之一, “英雄榜”创办人安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次国内的商业格斗赛中,他曾看到运动员快被对手勒得昏厥过去,裁判仍然没有喊停。“不少裁判缺乏综合格斗比赛经验,误判,错判,增加了动员的安全风险。”
运动员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医疗保障同样令人担忧。搏击主持人韩彬曾提到,国内很多比赛不规范,现场通常就一两个医生,现场连个救护车都没有。
“有些比赛中医生很没经验,当运动员被击倒后,现场医生竟然发呆。”在美国多年的安迪说,国外职业搏击赛事对选手有着一套严格的赛前和赛后监管措施。不仅赛前要对参赛者进行全面检查,如果比赛选手被KO(击倒) 的话,不管伤势是否严重都会被强制休息。此外,每场比赛,场外至少要用两辆救护车,以防一辆救护车运送伤员未归,又有新的伤员出现。
尽管有种种不足,刘小红还是认为,多年来的极低死亡率说明比赛的安全性与内容的精彩激烈并非不可兼得,中国搏击职业化商业化的路肯定没错。 ★
棍棒阴影里的武校江湖
2011年年底,因教练打人事件,武校的管理模式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在武校数以万计的习武者中,武术冠军屈指可数,更多的人流向社会,与职业武术擦肩而过
本刊记者/刘子倩 特约撰稿/张凯
(发自河南登封)
2011年12月12日这天上午,16岁的高明一如往常参加散打训练。中午训练结束,高明刚刚走出训练场就接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电话:上官鹏飞死了。
上官鹏飞是高明的偶像,不仅是因为上官的成绩突出,还因为他俩都有着相似的武校学习经历。已进入专业散打队的高明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在此之前,散打运动员从来没有因比赛受伤死亡。
郁闷远没有结束。三天之后,一组题为《河南某武校暴打学生,画面惨烈皮破血流》的照片在网上曝光,高明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母校,而一年多前,他也曾经有着类似的挨打经历。
从进武校习武到如今的专业队,高明的每一步都是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完成,虽然从教练到队友都认为他极具习武天赋,但上官鹏飞的死还是让他对前景感到悲观。他曾想过放弃,尽管如今他已是沿海某市的青少年散打冠军。
如同大多数武校毕业的学生一样,他对母校的情感很复杂,有时候甚至有点“恨”。那些棍棒打在身上的“啪啪”响声,是他抹不掉的梦魇。
相比之下,29岁的张帅可要乐观得多。这位北京奥运会武术比赛56公斤级散打冠军(散打为北京奥运会特设项目,金牌不计入总数),从小痴迷武术,对母校心存感激,尽管在学习期间也曾遭遇棍棒之苦,但他将此视为成长的阶梯。
教练打学生事件曝光之后,武术学校频遭公众诟病。虽然多数武校采取的是现代化教育,但中国武术的师承传统以及古老的庭院式训诫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现代武校。“棍棒底下出高徒”成为行业内不争的事实。
问题少年被送进武校
许多武校学生都是对学习失去兴趣的“问题少年”,进入武校似乎成为这些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孩子的最佳选择。高明就是其中之一。
2010年初,高明的父母把他送进了登封一家知名武校。像许多刚进去的孩子一样,高明对校内封闭的生活并不适应:16个孩子挤在一间寝室中,夏天只有两个电扇,晚上热得睡不着。而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跑操,随后就是一天紧张的训练。
对于这些独生子而言,训练是残酷的。夏天,在太阳底下一晒就是两个小时,所有人都被晒得蜕了一层皮。高明说,到了冬天,训练时也只能穿短袖,手脚长冻疮便成了家常便饭。
不过让高明最为恐惧的是违反校规的惩罚。这所武校规定,学生不得使用手机、MP4,不准打架、吸烟、看小说。如有违反,便会遭教练的棍棒“伺候”。同时,训练动作做错或者偷懒,同样会被打。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练一般使用少林棍,最少打五棍,打多少和下手轻重要看教练的心情。
不过,这不是最惨的。学生最怕被“保卫科”的工作人员抓住。“若被保卫科的抓到,可能面临着挨三顿打。”高明说。捉住犯错的学生,保卫科负责人往往先“收拾”一顿,再叫来分管这个班级的“部长”(实际为人事处处长,每位处长分管几个班级)。“部长”上来也是一顿拳脚,然后再喊管理班级的教练。一般情况下,最后教练出面都会觉得没有面子,将学生领回去后,免不了又是一顿“棍棒大餐”。
在高明的记忆中,被打的学员有口鼻流血的,有也当场晕倒的,还有被打得送到医务室输液的。“他们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没人敢还手。”高明说,如果发现逃跑,打得往往会更狠。有学员不服,教练就会让其他学生按住四肢,他再动手。
2010年一年,高明曾被教练收拾了三次。最严重的一次,他前后被教练打了26棍,屁股上裂了一条数公分长的口子,不得不趴在床上呆了一个星期,每次上厕所都要人搀扶。
“为了杀一儆百,教练们教训违规严重的学生前,往往会将上百名学生集合起来,让大家集体‘观摩’。”高明说,“大家都不忍心看,也没人敢求情。”
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上曝光的图片至少在一年多前,他就曾在同学的QQ空间里看过。
离开武校13年的张帅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因为动作不规范,他也经常挨教练打,并习以为常。在武校,体罚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学员几乎无人幸免。而如今已是小龙武院教练的杨道刚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从来不体罚学生,虽然当年他是被教练打过来的。“我们当年如果不被打,就觉得没有受到教练的重视,可现在不同了,更需要思想上的引导。”
登封武术协会秘书长郑跃峰也对体罚现象颇为头疼。他多次到武校作“习武尚德”的讲座,并在每月的武校馆长会议上三令五申。“我经常说,打骂学生是教练黔驴技穷的表现。”
在武校,学生难管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仅靠说服教育肯定力度不够,”一位武校负责人说,一些胆大的学生甚至抱着六楼窗外的塑料下水管道一下子滑到一楼。“如果孩子出了问题,还不是学校的责任,打学生两下又能怎样。”
一所武校一位60岁的门卫甚至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他脸上的伤疤。他因劝阻学生深夜外出,而遭学生殴打。
显然,仅靠暴力很难解决问题,反而埋下隐患。在高明眼中,武校更像是一个江湖,武林盟主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而江湖中人必须遵守规矩,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
从“业余班”到“武术集团”
20多年的发展,民间武校已发展成为集培训、比赛、演艺为一体的多元化产业链。
事实上,张帅可与高明是怀揣着不同的梦想来到登封的武校。前者从小酷爱武术,家境贫寒,希望靠武术改变人生命运;后者则是家境殷实的“问题少年”,家长希望武校严格的管理能给孩子带来改变。他俩正是代表了前来学武的两类人。
大批如张帅可一样对武术痴迷的人存在,推动了登封武校井喷式的发展。然而,武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登封市体育局工会主席、登封武术协会秘书长郑跃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少林寺和尚就开始在附近的少林寺中学教武术课。1958年,登封县业余武术体校成立,成为现代少林武术传播的重要阵地。文革浩劫中,刚刚起步的武校遭受重创,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得以恢复。1980年,登封县成立登封县少林武术体校,招收了22名学生,郑跃峰便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当时干部工资一月工资才二十多块,而他们22名同学的补助就有18元。1981年11月,《参考消息》报道了这家武校,第二年有一百多人专程来此报名学武。
此时,后来塔沟武校的创始人刘宝山也开始在家里招收徒弟。
对民间武校的推波助澜作用的是1982年电影《少林寺》的播出。随后,少林功夫红遍大江南北,慕名而来的习武人越来越多,登封的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最多时甚至“五步一馆、十步一校”。
《少林寺》热映的第二年,张帅可出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深受这部电影影响而最终学习武术的。
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假和尚、假拳师也开办武校也借机敛财。最终,登封市取缔了45所武校,仅保留了6所。到了1990年代,功夫热仍未减退,每年的人数还在增长。1995年,16岁的杨道刚从安徽老家只身来到登封,成为登封少林寺武术学校(少林寺小龙武院的前身)的一名学员。他来学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家人不再受同村人的欺负。在此之前,他切身感受到了舅舅来登封学武前后在村中地位天壤之别的变化。就在这一年,日后的“麻烦制造者”高明出生了,最终难逃被家人强行送进了武校的命运。而1996年,14岁的张帅可也进入塔沟武校,开始了两年多的武校生活。
郑跃峰说,经过近20年的发展,登封如今已有包括塔沟、鹅坡、小龙、武僧团等武术教育集团在内的52所武校,6万多名学员,教练多达8千余人,形成集培训、比赛、演艺为一体的多元化武校产业链。
“武僧团成立最晚却发展最快。它打着武僧团的概念,事实上仅是一家私人公司。”郑跃峰说。
习武人的“江湖路”
武校林立的繁荣背后,武校江湖的某些不良习气开始影响着越来越多学员的人生。
2004年,登封市第一武馆的教练乔文明因琐碎小事对学生不满,并拿学生“练手”,造成该学生头部重伤,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06年,登封市某武校教练发现学生私自外出,当即以违反校规为由,用手掌、勾拳、提膝、弹踢等武术动作,对学生进行殴打体罚,致其中一名学生当场晕倒,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07年,登封某武校教练为了给即将毕业的学生留纪念,用烟头给42名学生的胳膊上烫下烙印,最终被警方行政拘留。
2010年,一位吉林母亲千里寻子,称其在登封某武校的儿子因受大师兄的欺负而出走。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武校,师兄欺负师弟也很常见,让其帮忙打饭甚至是洗衣服。
事实上,在2008年以前,登封武校在当地曾一度名声很坏。一些煤矿老板与百姓发生矛盾,便会打电话找武校的教练带上学生前来助阵。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教练甚至带着学生还会干预别人家庭的纠纷。
“那时候登封哪里有纠纷,只要有年轻人出现,就会被认为是武校的学生。”郑跃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严厉整治,自2008年之后,这一现象便基本杜绝了。
其实,在这个武术江湖之中,想得到江湖人士认可,还要靠实力说话。在郑跃峰看来,原本强身健体的武术被赋予了浓重的对抗色彩。这是武术的大趋势,打倒对方也是意志品质的体现。当然,在以成败论英雄的擂台上,只有战胜对手才能获得奖金,赢得尊重和认可。
张帅可告诉记者,其实武术散打的商业比赛奖金也不高,有的只有几千块钱,但站在擂台上的选手大多不是为钱,而是喜欢这个职业,想以此证明自己。
对于所有武校的学生而言,都要面对的就是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毕竟最终靠武术吃饭的人少之又少。小龙武院教练杨道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正走上专业化道路的屈指可数,能成为冠军的更是凤毛麟角。
高明与他的同学曾不止一次地为出路而痛苦:“大家都在想,为什么受了这么多苦,最后还没有一个好的归宿?”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高明和他室友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通过训练,原来的“刺头”变得越来越少了。但现实仍旧残酷的,武校毕业后,有的进入专业队,有的当兵入伍,还有的当起了保安,而更多的返回家乡,甚至有的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5月,登封某武校6名学员学武四年之后,没有找到合适工作,便开始结伙抢劫。而此案办案民警亦称,武校学生犯罪目前已呈上升趋势。
除了学生,武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郑跃峰分析说,其他的技能培训周期短,见效快,而学武至少也要三年左右时间,周期相对较长,另外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父母很少再将子女送到武校受苦。所以,几年来,登封武校数量锐减,武校也过了赚钱的黄金期,如今已进入薄利时代。
为了竞争有限的生源,武校间除了价格战外,有的会雇用招生“贩子”到外地招揽生源。而郑跃峰每年都会收到针对招生“贩子”的投诉多达上百起,武校生源争夺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瑕不掩瑜,武校的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影响登封人拥有一颗成为世界武术之都的勃勃雄心。登封体育局2006年制定的《登封市武术产业发展规划》中写道,到2015年登封市在校武术学员将达到10万人,形成十大武术产业集团,并逐步形成跨国集团,并打造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武术训练基地,使少林武术覆盖全球。
如今,张帅可已成功转型为河南省散打队的助理教练,杨道刚同样坚守在教练位置上,只有高明想放弃。在他看来,即便拿到武术冠军又能怎样?用不了两年时间,江湖上就不会再有你的消息。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高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