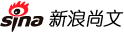城市形象“均贫富”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8日 09:26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真正海纳百川的上海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花3块钱吃到一碗葱油拌面,也可以花3000块听一场安德烈·波切利的演唱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零点,黑夜与白昼在此交替,梦幻与现实在此同行……”熟悉的音乐过后,上海最著名的电台午夜情感节目《相伴到黎明》开始了。
流浪汉“老东北”把收音机声音调大些,撮起一筷子猪蹄冻,就着瓶子啜一口“双沟镇老白干”,眯起了眼睛。
“老东北”是一个在档案中不存在的人,他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51岁。“除了港澳台藏,走遍了全中国!”
最终他“定居”在上海繁华的徐家汇商业区,最喜欢睡觉的地方是天钥桥路一家时装店门口。
正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举办的世博会,并没有对流浪汉们下逐客令。
2009年11月,1987年普利策奖得主迈克尔·帕克斯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们交流如何报道世博。“我最想知道的是—— ”这位《洛杉矶时报》的前总编辑放慢了语速,注视着学生们,“市政府将如何‘处理’流浪汉?”
帕克斯问:“世博会是上海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良机,会允许流浪汉为其抹黑吗?”
城市有没有容纳乞丐的自信心
“老东北”的存在感是以上设问的答案。
“我在上海十几年了,在徐汇区这一片,只要遵纪守法,城管不管,保安、交警见了面还跟我打招呼。”“老东北”说。
存在感也是市民给的。时装店老板娘每次有废纸板和废塑料都留给他;去吃面,店伙计会多给他加一只荷包蛋;“不扰民”有了信用,还可以在小卖部赊账买酒。
天钥桥路1号是麦当劳,天钥桥路123号是肯德基,每天零点过后,在这里过夜的人使这两家快餐店像候车室一样热闹。
3月19日,这家麦当劳的员工因为驱逐一名流浪汉被刺死。流浪汉并未因为这件事的阴影而减少对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光顾。过了午夜,警察偶尔会来查身份证,并不过多干涉。一名自称是“大食代”厨师的过夜者说,4个月前,这家店里的流民与顾客起了冲突,“110来了,调停后就走了。”
之后,肯德基开始请保安,甘肃天水人师继高就是那时候来的,“店里开会规定,进门即是客,不得驱逐。”晚上10点到翌早6时,师继高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别人的睡姿,“坐起来睡,脚不得放在椅子上。”
此时,“老东北”已枕在麻袋包上进入梦乡,包里是这几天拾荒拾到的塑料瓶。这些塑料被回收后可拉出弹性很高的丝,常用于填充毛绒玩具或抱枕,很多女孩抱着它才能安心入睡。
夜深人静,天钥桥路上的住户各得其所地睡着了。这应该是回答了帕克斯的疑问。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评论说:“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如果连容纳乞丐的自信心都没有,是愧对这个称谓的。”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说:“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建议城市开设贫民区,承认和保障城市贫民的居住自由,却遭到了猛烈攻击,仿佛贫民区是城市的污点。这恰恰忽视了梦想和现实的差距:城市里没有贫民区,这是梦想;贫民应该有居住贫民区的权利,不是流离失所,这是现实。”
城市空间的贫富分割
上海大学教授林少雄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认为城市形象承认两极分化只是最基本的,防止城市形象造成两极分化是更重要的。“城市形象某种意义上成了两极分化的根源。”
每次站在象征这座摩登城市的“三高”——上海中心、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 之间,林少雄都感觉自己是被排斥的:“除了永是高峰的车流和隐身于这些楼宇并只在早晚上下班时间匆匆来往道路上的白领人潮之外,这里令人感到一种空虚。”
台湾大学学者钟欣倩研究认为,摩天楼隐含着一种都市空间上的不均等,它通常为精英和富人所专享,而将平民置于被排除、被边缘化的地位。
然而,不断刷新纪录的“城市天际线”正是中国城市打造国际形象的手段之一,这种竞逐最高建筑的欲望,向人们印证着一座城市成为全球都会的合法性。
站在450米高的广州新电视塔观景台上,向北望去,与它齐肩耸立的432米高的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在夕阳的余晖中闪耀着光芒。这两座初落成的广州新地标,将借亚运之机,向世界展现珠江新城CBD堪与上海浦东、香港中环和美国曼哈顿等国际金融商贸中心媲美的显赫气质。
包括广州双子塔西塔在内,现今世界已建成的10座最高摩天楼中,有6座在中国。而全球在建的摩天楼前100名中,中国城市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仅天津就有13座,重庆有7座,沈阳有6座。最高的达到600米,最低的也不下300米。
与摩天楼的境遇相似,作为杭州形象的西湖最近也面临着沦为少数富人后花园的窘境。湖边许多名胜古迹和名人故居近年来悄然化身成了高消费的私房餐厅和高档会所。普通游客只能止步于底层或前厅,要深入参观,不是被告知“已被个人租用”,就是要达到会所设置的至少500元的最低消费。
西南交大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钱志鸿说:“打造城市形象工程一般选择在城市中心区,挑优势区位、好的方向优先开发,公共资源也优先配置,这样开发的楼盘容易卖出。而区位不好的,工人工厂集中的地方,政府就避开开发或者滞后开发,这里的公共服务、居住条件和治安状况都是落后的。这种情况在成都、北京、上海都存在。”
市政工程的嫌贫爱富
城市空间上的两极化,必然造成配套设施的贫富不均。
随着世博会的到来,上海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跃升为420公里,“已经位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三,这些都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形象。”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告诉本刊。
然而,有市民反映,世博前新启用的地铁11号线在通往北边高档社区的嘉定新城附近,每步行15分钟的路程就有一个地铁口,而在南边老平民区密集的地带,地铁站点却分设得很远。
地铁10号线也有同样的现象。在新江湾城以北的几站,地铁入口均设置在距离高档花园住宅很近的地带,而周边居民密集的普通社区,步行到地铁至少要20分钟。
世博前夕,上海市内环的所有公交车全部实现了空调化。但这个问题在2006年刚提出来时,是颇受争议的。当时有近半数的受访者对公交空调化投了反对票,认为此举大幅增加了市民出行成本。
近年来,许多城市为了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形象,大力推行公交空调化。起初,有的地方还采取空调车和非空调车“间着开”的方式,一些通常依靠公交出行的低收入者还可以选择多等待15分钟到半个小时,只为每次能省下一元钱的交通费。但后来,“清一色”的空调车逐渐完全取代了普通车。有南京市民感叹,强制实行的公交空调化连穷人的“苦等权”也剥夺了。
与此伴随的是出租车车型的大跃进,杭州、义乌、厦门等城市试图直接跨入排量“2.0时代”。
钱志鸿说:“高速公路、高档文化中心等公共设施,是为富人和中产阶级服务的,他们对这些设施的利用率最高,穷人没钱买车,也没时间休闲。他们被边缘化,在城市中是被排斥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侵占了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
林少雄说:“真正海纳百川的上海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花3块钱吃到一碗葱油拌面,也可以花3000块听一场安德烈·波切利的演唱会。”
“这里面住的都是有钱人吧?”
修地铁、换出租车、粉刷外立面,是将要举办大型活动的城市必做的规定动作,无论是奥运后的北京、世博中的上海,还是亚运前的广州。
这招似乎有些效果。申花足球俱乐部外援阿德拉尔多每次在高架路上看到尖屋顶的老房子都会问:“这里面住的都是有钱人吧?”不同的同车人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让这名巴西人很困惑。
这是上海“平改坡”工程的杰作,四四方方、类似“火柴盒”的旧式6层楼的顶上塑一个老洋房的帽子,还有假烟囱、假天窗,再用温馨的灯带一勾勒,的确怀旧又高档。
但“平改坡”工程在广州却遭遇了很大的阻力。为了迎亚运,广州市政府对机场高速路、港粤之间铁路两侧以及外国人最可能光顾的豪华宾馆四周的1000多座楼房进行了“平顶改坡顶”形象改造。据说,给机场航线范围内的房屋“戴帽子”后,就能让全世界乘飞机到广州的人,在起降时看到五颜六色的美丽屋顶。
这项工程引起了部分居民的不满,因为传统平顶是居民晾晒衣服、谷物和腊味的好地方,也适合放置太阳能热水器。有人为此站在屋顶上抗议。
上海市民却对这种“穿衣戴帽”感恩戴德。承担着上海“西大门”进出市区重任的武宁路桥,斥以巨资改造,借鉴了位于法国塞纳河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树起4座27米高的艾奥尼克式立柱,顶部用铜浇注,再加上表面贴金的4个雕塑。
桥下的老公房与这座桥的辉煌十分不配,施工方又赶在世博前粉刷了外立面,猩红色的欧式砖,足以让老外们相信这是一片富人区。居民对这个方案拍手欢迎的原因很简单:“利于房产升值。”
“与居民的利益一致时还好说,但当改善形象的诉求与居民不一致时,就不宜用一刀切的方式强推。”林少雄说,“请记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话:‘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人间天堂’。驱逐流浪汉、建无摊城市,莫不如此。”
将社会凝聚力与城市竞争力同等看待
钱志鸿分析了城市形象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
城市形象战略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西方的城市形象运动,欧洲和北美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逆工业化,需要通过打造优良城市形象吸引和争夺人才、资本入驻,增强城市竞争力。而我国并未遵循西方城市发展的完整过程,直接进入了创造财富、削减福利、注重吸引投资的模式。
西方的形象运动同样造成新的两极化,“由于忽视社会平等,在美国产生了新的底层阶级,形成了所谓的二元城市;在欧洲,这一发展政策则导致了明显的社会极化,形成了新的城市贫困现象。”
“城市形象战略虽然总体上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但并不必然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如果社会目标缺位,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城市资源向精英阶层倾斜,使城市精英成为这一战略的主要受益者。”钱志鸿说,“现在,西方已经将社会凝聚力与城市竞争力同等看待,注重城市形象战略中的社会目标,需要通过社会‘内涵式’发展来实现。”
这个所谓的“内涵式”,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改革处处长钱智向本刊介绍了一个实例: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街道社区,20年前曾经是一个贫穷杂乱的动迁基地,没有豪华建筑,没有大型商业。基层政府通过发动居民自治,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委托第三方代理等方式,将这条“穷街”建设成为具有幸福感的和谐社区。
每天中午,一个特别的“车轮食堂”都会开入这里。几名受聘用的社区下岗工人从三轮车上搬下一份份盒饭,将它们送到社区里660位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里,还会顺手带走老人家中的垃圾。近年来,有不少邻近社区的老人,特地冲着“车轮食堂”搬到这里居住。
钱智说,临汾街道社区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全覆盖。“这里政府并没有搞什么形象战略,但国外很多考察团都会来这里学习社区建设的经验,形象自己树立了起来。”■
(特约撰稿邓之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