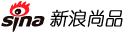孩子的世界容不下太多谎言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8月23日 10:20 21世纪经济报道
弗朗索瓦•特吕弗在他的影评集《我生命中的电影》中写到:“我的头两百部电影都是逃学时看的,而且都是不付钱偷偷溜进电影院——从紧急出口或者厕所窗户——或者趁父母晚上外出时去看的(但我得在他们回家前就先躺回被窝,装出睡觉的样子)。为了这些快乐的时光,我付出了假装胃疼、抽筋、神经性头疼的代价,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只会令看电影时引发的情感变得更加热烈。”
 四百击海报
四百击海报在那部法国新浪潮的发轫之作《四百击》中,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一幕看电影的画面,是主人公安东尼在家里点燃了一只蜡烛,祭奠巴尔扎克,不小心烧了神龛。父母赶紧扑灭了火,倒是没有过多责怪安东尼,反而决定带他去电影院去看电影。那是整部电影中唯一的家庭欢乐曲,他们从电影回来,互相模仿电影中的场景,笑声洒满了一路。很奇怪的是,也许正是这种欢乐的基调,反而显得几分超现实的意味。在电影的大部分场景中,安东尼都是调皮捣蛋,逃课,戏弄老师,偷东西,直到进了少管所。他与父母的关系一直都马马虎虎。
但是特吕弗开始并没有过多交代他们的家庭背景,直到影片快结束时,安东尼在少管所,面对过来的心理辅导员,才说出了他与父母的故事。你会注意到那个场景,安东尼面对着镜头时,总是低着头,要不就是左顾右看,漫不经心地玩着什么。我们能感觉到那种漫不经心中蕴含着一种多么强烈的感情释放和心理创伤。从没人会在意他的故事和感受。母亲未婚先孕,想要堕胎,被祖母发现才保住了孩子。继父对他还不错,但整日忙于工作,也没有更深的感情。他八岁之前一直跟着祖母生活,八岁之后回到父母身边,也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他与父母之间有着很深的裂痕,但这个分崩离析的家庭,在他逃学的路上看到母亲与同事亲吻时,已经坍塌了。母亲心虚地讨好他,让他“分享”他们之间的秘密,那个镜头中,安东尼清澈的眼神直视着镜头,好像看穿了这个谎言遍地的世界……
在少管所,心理辅导员问安东尼,为什么经常对父母撒谎?他的回答仍然是一幅漫不经心的口气:因为就算我说了真话他们也不相信。在孩子的世界中,撒谎的快乐源于一种延迟性的满足。为了营造出一种短期的幸福和快乐,撒谎仿佛一种生存的技能训练。我们都会留意到那个场景,他逃学的路上看到了妈妈与她的同事亲吻。第二天去了学校,老师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来。他告诉老师,他的母亲死了。为什么不说是爸爸死了?母亲后来很不忿地问爸爸,爸爸耸耸肩,说也许他喜欢我。母亲明明知道答案的,她的反问反而是一种道德上的心虚。孩子的世界中容不下太多的谎言,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无忧无虑的自由生活。尽管一次次遭受挨打挨罚,他和他的朋友每次逃学在路上,或者夜宿街头的时候,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行动中感受到他们真正的快乐,一种孤独,不被人理解的快乐。仿佛他们的童年要被扼杀了,剩下的时日中要赶紧寻找快乐。
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一切。他偷了一部打字机,没卖出去,鬼使神差地想还回去,结果被抓了。我们能从那个铁窗后面的镜头中看到他脸上的那种面无表情的表情。那是这部电影中最富有冲击力的一个镜头,而且正对应了影片结尾时,安东尼逃出了少管所,一路奔跑到了海边。他不停地奔跑,镜头中的空间变得开阔起来,然后镜头定格在他的脸之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他站在了少年与成年,过去与未来的门槛上。那种神情是一种找不到方向的表情,一种生活中的逃亡的表情,一种困惑而孤独的表情。他过早了尝到了生活的滋味。
《四百击》的片头中写着要把这部电影献给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当特吕弗处于人生早年的低谷时,正是巴赞将他这个没有父亲的年轻人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帮助他拜托了动荡不安的生活,走上了电影创作之路,先是成为了一个影评人,然后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导演,在二十七岁之前创作了这部电影。《四百击》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他早年生活的自传。但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任何人都能从中找到会心一笑的认同点,但这种感情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感情的疏离。我们远远观望着别人的童年,回想起自己的,另一种形式的童年,那是一种童年的丧失,纯真的堕落,谎言与真相无法区分的世界。
相对于新浪潮电影中的其他导演,特吕弗在这部电影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激情。美国的罗杰•伊伯特评论这部电影时说:“许多人认为法国新浪潮标志着古典电影与现代的分水岭,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特吕弗大概是最受欢迎的现代导演之一,他的影片能令人感受到电影创作最深沉、最饱满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