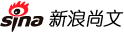一个法国摄影师的中国眼睛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3日 09:20 《小康》杂志
导语:马克·吕布来到了当时铁桶一般封闭的中国,他带着西方人接触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用陌生的眼睛告诉我们,原来照片可以不用提前摆好姿势,他让我们眼前一亮
文|《小康》记者 管方方
1957年去延安时,他拍下一张照片,主角是毛泽东的那张床;196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拍下中国民众在天安门前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1992年,他将镜头对准《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型宣传画,拍下脚手架上一名工人为画像着色;1994年,他拍下深圳建议人们购买股票的广告,下面是撑伞路过的行人,广告板上的金币则像雨点般落在木质人行道上……
他看过黄浦江上的风帆,登过8次黄山,对北京全聚德的方位了如指掌,但他却始终不会讲中文。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和许多 “年轻的”中国摄影家成为忘年交,并被后者送了个可爱外号“老马克”。
关于“老马克”,众所周知的经历是:1923年,一个叫做马克·吕布的男孩出生于法国里昂,14岁时他从父亲那里获得一台柯达相机,从此便走上摄影之路。
上世纪50年代,身处巴黎的马克·吕布得到摄影大师卡蒂埃·布列松的赏识,在其帮助下加入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在玛格南的一众摄影师中,他是与亚洲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一位——1955年他驾车6个月从巴黎经土耳其至印度。在印度呆上一年后,他来到中国,此后往返中国达20次之多。
马克·吕布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2010年3月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个人摄影回顾展。北京,是其展出的第二站。
对观看和拍摄暴力心怀抵触
这场展览名为《直觉的瞬息》。“瞬息”这个概念来自布列松。“马克·吕布师承布列松,布列松是‘决定性瞬间’理论的提出者。所谓‘决定性瞬间’,就是照片从紧张到达最高潮,然后开始松弛的一刹那。他们主张的是,照片就应该如实记录,而非摆拍。”著名摄影记者唐师曾这样对本刊说。
马克·吕布无疑是个“瞬息”大师。首先,他选择了最适合表现“瞬息”的工具。马克在传记中称自己是个害羞寡言的人,惧怕与人交往,一度逃避生活。他用以与周遭发生关系的工具,是一只1984年产的莱卡M6相机。
在唐师曾看来,“莱卡M系列不带反光、单镜头、很小、黑机身,这些外部构成使得它能最小限度地打扰被拍摄者。”因而,那些“决定性瞬间”也就更为真实地被记录下来。
比如1957年,马克·吕布在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上,拍下了关于中国的第一张照片,对象是一名身着黑青色中式衣裤的女人。马克为照片添加的注释是:“体面而端庄的女农民。”
在本次北京展览中,与“广州火车上的中国女人”并排摆放的,还有1958年东京火车上睡着的日本女人,素衣、细眉、微微凌乱的卷发;1971年上海芭蕾学校的女学生,白衬衣、长辫子、胸前别着革命徽章;1958年东京百货公司里掩嘴而笑的优雅妇女;1971年加尔各答难民营里哺乳的印度妇女,眼神平静又孤独,裸露的乳房泛着暗色的光……
“我到处去看,我热爱那些美丽的脸,热爱奇异而无垠的风光。”马克·吕布数次强调自己不打算成为那种“献身政治事业”的摄影师,“我更像一个四处漫步的流浪者,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天地间慢慢游荡。”
“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摄影师,比如罗伯特·卡帕或尤金·史密斯比起来,马克·吕布可能性格没有那么强悍。他并不是直接冲到战争和流血最前线的那种摄影师。” 唐师曾说。
对观看和拍摄暴力心怀抵触,使得马克·吕布曾在面对处决被俘虏的恐怖分子时,不是举起相机,而是合上镜头跑去找来印度官员求助。身为一名玛格南摄影师,马克·吕布更倾向于捕捉生活中幽微、细致的点滴,表现政治或文化的本质。
马克·吕布的成名作是那张《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他在自传里这样记录:“布列松给了我一个传统的取景器,当时我刚到巴黎。我在相机里塞了一卷底片,就跑到埃菲尔铁塔那里溜达——真是个货真价实的外地人!我看到一群握着刷子的油漆工,与其说他们是刷漆工,还不如说更像杂技演员。我特别害羞,不敢上前同他们说话。正当我试着构图的时候,一个工人突然头朝下出现在我的取景器里。后来我把小样拿给罗伯特·卡帕看,他圈出一张,然后卖给了《生活》杂志。这就是我第一张发表的引以为豪的作品。”
来到中国,记录中国
“马克·吕布是最早一批接触中国的玛格南摄影师”,摄影评论家李媚女士说:“他的作品告诉了当年的中国人,一种不同的观看身边生活的方式,从此中国摄影家开始将镜头对准日常生活,而从前我们不是这样。”李媚曾创办和主编深刻影响中国摄影史的杂志《现代摄影》。1989年第二期的《现代摄影》上,以大篇幅将马克·吕布第一次介绍给中国摄影人。
马克·吕布来到中国、记录中国,其最大的意义,在著名摄影评论人和策展人鲍昆看来,是“他来到了当时铁桶一般封闭的中国,他带着西方人接触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用陌生的眼睛告诉我们,原来照片可以不用提前摆好姿势,原来照片可以这么拍,他让我们眼前一亮。”
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纪实摄影的苍白无力,李媚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加以说明。“1976年唐山地震时,摄影家林永惠是现场唯一的见证人,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制约,摄影家没有将镜头对准一幕幕灾难场面,而只是拍下了符合宣传口径的画面,结果,他错过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而中国摄影则给历史留下了永远的空白。”
于是,到了对摄影价值重新思考的1980年代,摄影家们开始试着掂量中国影像事业的遗憾,他们自然而然将目光锁定在西方,锁定在“老朋友”法国人马克·吕布身上。
马克·吕布抓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拍过北京街道上三个手臂交勾着并行的女孩、拍过1957年拥挤的上海大街、拍过1965年端着木枪的沈阳少年、拍过街头艺人表演“胸口碎大石”、拍过烟囱旁举手示意的主席雕像、拍过解放初走在王府井大街上的没落贵族。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他掀动快门,为中国人留下了我们刚好经历过的时光。
从过度阐释到回归常识
在鲍昆看来,马克·吕布的照片之所以一次次打动中国人,更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为那些照片记下了 “历史上或生活中让我们心里颤动的事物”。“但马克·吕布并不是他所处时代最具典型性的摄影家。作为一个西方人,猛一下进入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东方国家,那种强烈的差异和撞击太明显了,如同城市人刚进入一个陌生的乡村,也会猛摁快门一样,并且视角独特。”鲍昆说道。
马克·吕布对上海情有独钟,1992年和2002年的中国之旅中他留下了大量关于上海的照片,它们被以对比的方式呈现在此次《直觉的瞬息》影展中。其中包括1993年上海街头的时髦少妇、坚固庞大现代的杨浦大桥、人头挨人头的节假日商场、傍晚时分穿着睡衣在弄堂里聊天的市民、铺天盖地的街头广告画、巨幅可口可乐标志和外滩时尚餐厅……事隔几十年后,一度认为已经拍够中国的马克·吕布,重新发现了正经历巨变的中国的摄影价值。这不再是那个神秘莫测的中国,这里演进的关于现代化的一切都似曾相识,同时又充满独特的东方矛盾,一些质朴的东西正在消失但并未殆尽,演变成另一些奇特的冲突表现体。
不可否认,马克·吕布用自己的镜头为我们呈现了50多年来发展中的中国。但针对马克这些近期照片的分量,摄影评论人鲍昆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西方摄影家拍中国,从前的优势叫做‘陌生的眼睛’,毕竟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是将题材和目光放在所谓‘宏大叙事’上,我们不关注身边小事。但在摄影极为普及和常识一步步得到回归的当下,这种‘陌生眼睛’的优势或许已不再明显。”
因此在鲍昆看来,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必过度阐释。理性思考,才能更为客观。
过度阐释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对摄影大师们职业行为的解读上。
某种程度上,出于对旅行的热爱和对神秘地域的向往,使得马克·吕布留下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国家及北非的照片。于是,人们总喜欢将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照片找出某种关联,试图牵引出不同宗教文化在人们生活里的烙印。
“我想马克·吕布用‘直觉’二字是恰当的,这只是摄影家的直觉。但你不能提升到一个什么高度,否则就太奇怪了。”唐师曾说道。
至于鲍昆则觉得,“在看待马克·吕布时,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所有过度阐释回归常识——无论他本身是不是一个具有强烈关怀意识的人,他的确一次次来到中国,他的职业使命使他恰好留下了关于中国的珍贵影像,那个年代我们都经历过这些影像,却见怪不怪,仅这一点,中国人也需要感谢马克·吕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