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 在V城致文学同代人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03日 13:49 东方早报
导语:与港台作家聊天,“董启章”是一个时常被提起的名字,从《天工开物》、《时间繁史》到目前还遥遥无期的《物种源始》,董启章闷头在家写了一部比一部厚的小说。原以为他像大多数香港作家一样,专注个人写作不管窗外事,没想到在刚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上,董启章发起吁请香港特区政府建香港文学馆,还在书展里连开两个演讲发表建馆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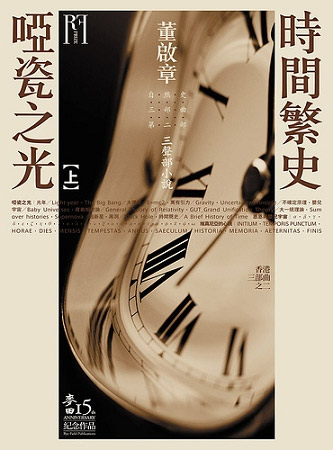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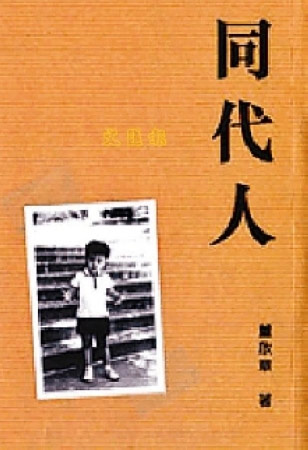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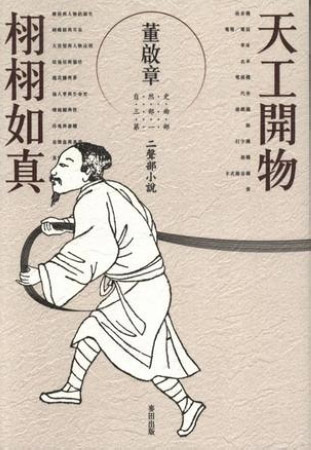
作为作家,《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被认为是董启章赠送给香港的礼物;作为社会活动分子,他还是希望香港文学能突破香港区域限制,在华语圈获得更多的认同,他倡议下的香港文学馆,在理想中应该能成为推动香港文学发展的根据地。
“在香港,靠文学为生、出名是天方夜谭。”
董启章的新作是《致同代人》,昔日的“同代人”在V城(董笔下的香港代名词)已转型成当红文化人,或者是拿着高薪的象牙塔中人,也或者不知道流落到了哪里……这些同代人的遭际是V城文学青年的必然命运:“其实大家都知道,在香港,靠文学为生、出名是天方夜谭。”董启章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坐在面前的董启章十分平静,“如果称我为小说家,对我来说会有点不自在。你在香港如果站出来大声说,‘我是小说家’,肯定有人会嘲笑你,‘你是谁啊?’小说家这个身份或者文学,在香港是得不到认同的。人家听你说是小说家,会问你写什么类型?武侠还是科幻?他们都是从通俗文学的方式理解小说创作。如果你说,你从事纯文学写作,他们就会不理解,‘还有人在写这种东西?’”正因为文学在香港从来都是那样边缘,所以就算只有几百个读者也不会有太大的失落,“反正不希冀有太多人看你的书,从这方面讲,我比台湾骆以军他们要幸运一点。”当然这里的幸运,也只是自我安慰。“在台湾,跟我同代的那些作家见证了文学衰落的整个过程,我能想像得到他们的压抑。前辈的成名作家曾经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但到了他们这一代,文学慢慢变得不太重要,而再年轻一辈,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文学理想了。”“他们有一个文学理想失落的过程,而我们香港这里从来都没怎么好过,所以大家心态反而比较好。香港作家从一开始就没有幻想通过文学创作会得到什么,我们都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
董启章的话听上去有点自欺欺人,毕竟对名和利不会有人拒绝。在曾经银行账户经常只剩下100多港币的日子,如果能得到一个文学大奖,总归可以死撑一段时间。所以当年莫言拿走香港红楼梦奖的时候,不少人嘀咕,这30万港元对莫言没啥意义,但董启章就可以靠着这笔钱过好长一段日子。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董启章和他的同代人生存状态并不太好,但他对未来是乐观的,“台湾的作家们非常担心文学慢慢死去。我们不这么认为,反正文学一直就是这样子,而且依然有年轻人不断加入文学创作队伍中来。这几年,文学爱好者慢慢多起来,年轻人对文学也更加活跃。香港有一些年轻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不同的东西,出于这种动机他们爱上文学,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我们需要做点事,理解、整理、推广香港文学。”
谈起前辈,董启章还是流露出一丝羡慕,“上一代的文学风气要好一些,当时还有一些文学刊物、同仁杂志,读者也蛮多,至少文学杂志都有几万份销量,这是很厉害的数字。”而大陆作家丰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也早有耳闻,“大陆的市场很大,作家怎么样都能活,作家有不同的渠道获得利益。”
当然董启章他们也并不是只有“反正就是这样了”的心态,“在香港,作家的工作非常个体化,其实对文学也不利,大家只专注个人写作,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文坛,让大家聚在一起。”也正因如此,至少内地读者对当代香港文学是异常陌生的。谈起香港文学,除了金庸、亦舒、黄易等通俗作家以及一批专栏作家,就像董启章自己迷惑小说家身份一样,香港真的还有纯文学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除了董启章,还有黄碧云、韩丽珠、叶辉等等,“但就是没有多少人知道,”董启章说,“很奇怪的是,香港本土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小说,所以我们的作品都是在台湾出版,相对台湾对我们比较了解,内地读者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除了这个原因,更重要的是香港作家过于自我,而且没有一个团体帮助推介文学,这就是我们发起成立香港文学馆的重要动机。”“大家渐渐觉得,我们需要做点事,理解、整理、推广香港文学。”
建香港文学馆是本届香港书展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些平时很少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作家们穿上统一的文化衫,高呼“香港需要文学馆”。“用文学馆凝聚一群年轻人推动写作,理解香港的故事和经验。”“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机构把香港文学和其他地区作交流,所以香港文学尽管也属于华语文学,但它与内地文学的交流几乎为零。因为没有一个代理机构,香港作家也不会跑到内地去宣传包装自己,所以没办法让别人了解香港到底有什么作家。”
广泛意义上的华语文学应该包括内地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马华文学和海外写作等,从空间上看华语文学可以像英语文学那样形态、内容非常丰富。但在现实中,华语文学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华语文学如果只有内地这一块,其活力就会丧失,不同地方的写作经验、生活经验可以丰富华语创作。当代英语文学能保持活力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他们除了英国文学外,还有爱尔兰文学、前殖民地文学先后兴起,推动了英语文学的发展。华语文学也可以这样。”不过,华语文学的交流直到现在才慢慢起步。
“写《物种源始》,太恐怖了。”
董启章是1960年代生人。如果有代际之说的话,内地、台湾、香港、马华地区分别诞生了一批知名60年代作家,比如大陆的毕飞宇、台湾的骆以军、香港的董启章、马华的黄锦树。相仿的年龄,各自不同的出生背景和成长经历,拼贴成一幅绚丽的华语文学地图。在《致同代人》中,董启章用文字想像着和他们进行文学的对话。
董启章的文学之路始于1992年,当时他在读研究生,“1992-1993年,香港《星岛日报》开设了一个文学副刊。这个副刊在香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它每天一个文学专版刊登年轻人的来稿。包括我在内很多没有写作经验的年轻人都在那里写作,这对年轻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董启章说,与内地相比,香港提供给年轻人的写作机会非常少,“就算是现在,我在香港也没有空间发表1万字的短篇小说。”
董启章最畅销的小说可能是校园题材的《练习册》,“《星岛日报》的副刊关了之后,那个编辑办了另一份学生报纸,约我们写校园题材,没想到《练习册》陆陆续续一直卖了10多年,大概有七八千的销量吧。”
对于这个数字,董启章很满足,他的最重要小说“自然三部曲”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自2005年出版以来共卖了五六千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近500页的篇幅,30万字的分量。董启章用三代人的书,构造出V城三代人的历史。
在印象中,自用童话方式写香港历史的西西和用《香港三部曲》终结自己香港写作的施叔青之后,香港年轻人的写作越来越陷于自我和都市碎片化,“我也许是香港极少数还在写香港历史的年轻作家,但我不认为自己是本土写作,我只是想从香港本土经验出发探索人类的普遍问题。”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普遍反映是很好读,但董启章却并不满意,“写完第一部后,我还是觉得写得太自我了,格局也太单一,所以在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里,我把自我彻底去除掉了。”这样的努力结果是,上下两册《时间繁史》销量只有2000多册。“《时间繁史》是我的一个实验,用广东话来写大篇幅的深刻对话,这对台湾读者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知道这样写会影响阅读,但我一定要去试验一下,现在总算遂愿了。”
董启章是有野心的,这从他正在写作中的“自然三部曲”第三部《物种源始》规划可见一斑,这部构想中的小说至少有三册以上,最后到底会呈现什么面貌和厚度,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目前完成了《物种源始》的第一部分《学习年代》,已经写了40多万字。”“写《物种源始》,太恐怖了。太厚,太恐怖。出版社只要愿意出版就行,就算只有几百个读者也不要紧。”
香港对文学作家的诅咒是,要在本城当作家活下去,你就必须干更多写作以外的“勾当”。过去,董启章为供养家庭也干过不少与写作无关的活,如今为了写《物种源始》,董启章推掉了赖以维生的学校兼职教学工作,也不接任何一个专栏,“我要把想到的所有意念,全部写到这部小说中去,而不是分散在不同作品和专栏中。”
“我的写作一直很平静,所以我不觉得太辛苦。”受到董启章的激励,更年青一代的香港本土作家或者文学爱好者,甘于寂寞和物质匮乏地走在文学路上,当然更多人只是迷恋那种文学氤氲而已,而这总归会散去的。
还好,至少《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最快年底就能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了,而《物种源始》让我们继续想像等待。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