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男人的独角戏:段奕宏 张译 李晨独家专访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12日 13:58 《环球生活》
导语:5月,火热的前戏,我用迷茫的双眼打量798的三个男人。从行伍微末到精忠报国,一支笔写不尽孤绝的青史,还有纷扰。所以,我们停下脚步,倾听着那些过往、现在和以后。
段奕宏:从“人精”到“妖孽”
 |
38天的坚守,人如死灰,饿得只剩下腹中的山呼海啸。不辣拿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兄弟们过来和龙文章靠在一起,“回家了,相互拉扯着点,腿脚都不利索。”孟烦了说。迷迷糊糊中发现有人奔向树堡,龙文章打掉了最后一颗子弹,率领大家赴死……救兵来了,大家无力地咀嚼着食物,哭了。走出树堡,阳光灿烂……
坐在798艺术区的一间咖啡吧里,段奕宏为我讲述着《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的结局。南天门决战这场戏,他们拍得很苦,从段奕宏放光的眼神中我可以读出他持续的兴奋,不过也有遗憾,因为龙文章等人的最终结局,电视剧并没有拍出来,而原著讲得很清楚:龙文章自杀了。
进入?走出!
《士兵突击》里的袁朗是一个典型的“人精”,《团长》里的龙文章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妖孽”。段奕宏这么评价两部让自己迅速火爆的片子所赋予的角色,其实二者是异曲同工的,都活得超现实,让人琢磨不透内心想法。一直在话剧舞台上奔波的段奕宏显然不怵这类“极致”角色,那场在虞啸卿面前“跳大神”引出自己身家的戏,他将人物的卑微、自私、不羁、张扬、胆怯全面地展现出来。
拍完《团长》,段奕宏觉得“更加清楚地发现了自己”,因为一个人的成熟,不仅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更多的是要经历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自己或许具备另一种潜力,才会听到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有让你挣扎、寂寞、迷茫、彷徨、质疑的时候,最终你选择了一条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路。
艰苦的过程难免使人在终点时还保持极度亢奋。段奕宏说自己在每天拍戏的间隙都很难走出来:“即便是现在片子都上映了,我呆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看似听着小野丽莎,喝着摩卡,但心还在禅达悸动。”段奕宏还讲了一个故事:某位记者曾约定在一天拍完戏后对他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但他迟迟走不出那种状态,不由自主带有一种龙文章的情绪。他邀请记者一块儿吃饭,人家推辞,说和其他人不熟。他一改平时的温柔,强硬地说:“什么熟不熟的,见了面就认识了!不去是吧?那采访再约!”事后,段奕宏很后悔。
现在,段奕宏基本走出了那种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我愿意走出来时,自然会去主动寻找一种方式来卸掉这部戏的精神压力。比如去拍另外一部戏。”
“闷骚”解读
采访的时候,我一直迟疑该不该向段奕宏提出“闷骚”这个话题,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骚”就是风骚的意思,总带些庸俗的联想。于是我试着换种方式,将“闷骚”安在了龙文章身上。老段乐了:“你就直说是段奕宏闷骚吧。”
段奕宏对这个词并不排斥,他把它归结为“心中极度渴望,可又在表面很克制。”仅是一种心理暗示,谈不上很错位的行动。按照老段的解释,“闷骚”其实是一种性感,是一种内涵,例如他本人喜欢莎拉·布莱曼、小野丽莎、陶喆的歌,却不排斥周杰伦,一些口水歌也听,音乐上的小资与大众相融合,其流露出的东西就是属于段奕宏的闷骚。
从另一种角度分析,段奕宏的闷骚或可解释为生活历练的结果。老段出生在新疆,18岁时曾疯狂地想报考中戏,原因很简单:因为能吃上好吃的。第一年没考上,一试就被刷下去了,他去天安门广场坐了一晚上等着看升旗,当时借了朋友的相机疯狂地拍照,这时一个武警过来摁住他:“兄弟,镜头盖没开呢。”失败让周围的人都在怀疑段奕宏是否具有演戏的天赋,他不想放弃,去搓果丹皮挣路费,一天7块钱,虽不算多,但很满足。在考上中戏那一刻,段奕宏想得最多的是,选择自己的理想,就应该去挨、去忍这种东西(磨难)。
大学的四年,段奕宏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话剧创作上,从来没有敲过导演的门,跑过组,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坚守,这是段奕宏给我的回答。只有投入到艺术表演中,他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也让那些虚荣和浮躁无处可藏。
因为坚守,所以放弃了很多;因为放弃了很多,所以他必须有一方净土来展示内心。龙文章在剧中经常念叨《诗经》中的篇章: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段奕宏正在用他的经历为我们缝制一件宽大的袍服,谈不上精致,却很有味道。
张译:小太爷的猫样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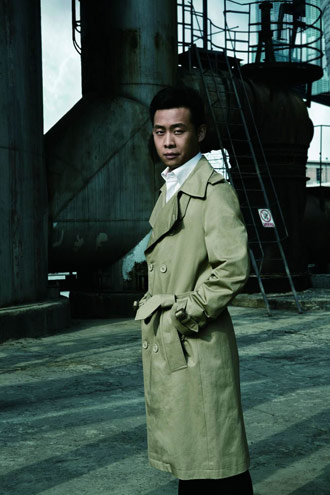 |
《团长》的最后一个镜头:孟烦了的原型——中国远征军老兵以一个刚毅的转身带给人们无数遐想;孟烦了的扮演者张译配完最后一段画外音,在镜头后露出微笑的面庞。
采访时,我怎么也无法将眼前这个温文尔雅、语气低沉、喜欢猫的男人与《团长》中那个油滑、贫嘴、带点小愤青、却又懦弱的孟烦了联系在一块儿。张译自称生活中的他完全不是剧中那种状态,特别是油滑,完全挨不上边。只是因为有了剧本,自己下苦功去理解,最终,“兵油子”形象得以诞生。“小太爷”张译也可以平静地陪伴着自己的猫。
60年与172天
“在24岁的时候,我在这里打了一场搏命的战斗,命运说只坚守两天,我们却守了38天,在第38天头上,我太累了,睡着了,这一觉我就睡了60年。”这是孟烦了为自己的远征军生活画上的最后一个注解。看起来很有诗意,但如果把整个拍片过程比作一场战役的话,那么在172天的拍摄接近终点的时候,张译真的有点撑不住了。
张译说他几乎不可能冷静的,以一个完全第三者的身份去看自己的片子,必须得想起关于自己和片子的一些事儿。他想的最多的是自己对角色的诠释。孟烦了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还会说ABC,脑袋也灵光,就是放到现在的社会也不落伍,他60年前就达到了这种状态,却只有从戎这一条路,这似乎只能用黑色幽默来解释。“他什么都看透了,因此愤怒,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只能以一张愤怒而恶毒的嘴去面对周围的一切,因为承担了更多的东西,所以他活得很累。”张译分析着孟烦了的性格特征。张译认为,龙文章和孟烦了就是一个人的两面,龙唱黑脸,孟唱红脸,互为补充,因此形成绝配。
有人说《士兵突击》的走红带有偶然性,《团长》则是必然的,因为前者是这帮演职人员从默默无闻开始起步,后者则是在一个高度上向上攀登。172天的拍摄就像是在登天梯。张译不否认这个说法,但也感慨,这登天梯的人太多了,可路只有这么点儿窄,他们这帮人赶上了优秀的剧本和编剧,遇见了挺棒的导演。毕竟和他们条件相当的演员,国内还有很多,没拍过什么好戏的大有人在。从这个角度上说,张译们无疑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