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中日关系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0日 10:31 人物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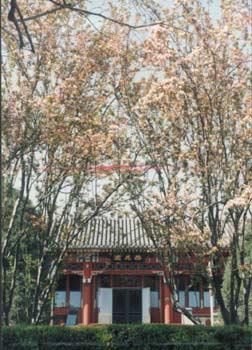 |
文/钱嘉东 王效贤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2008年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此时此刻,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二者联系起来,回忆起周总理生前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大量工作和不朽贡献。
高瞻远瞩着眼未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一成立,即向全世界宣告:我国愿与一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与我国建交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少数刚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获得独立的亚洲邻国。西方国家中,除几个西北欧国家与我国建交外,绝大多数都拒不承认我国。特别是美国对我国采取孤立、封锁、禁运,企图扼杀新中国的敌对态度,直至22年后迫于内外形势才不得不承认现实,前来叩敲新中国的大门。
至于日本,当时还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不能不听命于美国,1951年在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上签字,次年又同台湾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了非法的和约。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自然不具备正常化的条件。
但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我国对于日本这个一衣带水并在历史上素有交往的近邻始终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我们并不期待在短期内有所突破,而是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相信两国关系最终是要正常化的。
我国的对日政策中,有两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严格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这是说,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二是正确对待两千年与50年的关系。这是说,中国人民一方面应牢记1895—1945年这50年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中日两国人民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史。
周恩来总理是上述政策的制定者,更是贯彻执行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初,当他开始有机会接见来自日本的朋友时,就反复向他们阐述我们的政策。
1953年9月,在第一次会见日本朋友、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周总理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中国愿意恢复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继续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并继续保持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外交关系,日本就会成为太平洋上不安定的因素,从而阻碍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周总理还说:“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有广阔的前途。”周总理的话通俗易懂,含义深刻,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善意和诚意:从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确处理中日关系。
周总理也经常以这些政策教育我们自己的同志。在外交部成立时,原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后改任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同志,在他1989年写的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50年代初,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开始了民间贸易,但障碍很多,进展不大。当时总理教导我们,对日本既要正视60年(编者注:原文如此,但总理经常说的是50年),但也要考虑两千年。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长达60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另一方面,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和日本打交道,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中国老百姓不答应;太勉强,日本政府也办不到。所以总理提出了“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方针。
由此可见,从那时起周总理就以他的远见卓识,勾画出了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蓝图。虽然一时还无法建立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但在我国的主动努力下,还是做了两件实质上属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大事: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送回了战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释放了全部在华日本战犯。
在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以后,有大批日本人来到中国大陆,至抗日战争结束时,约有130万日侨留居中国。除大批日侨在1948年前已回国外,新中国成立后留下来的还有约3万人。1950年冬,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出席在摩纳哥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时,周总理指示她主动同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岛津忠承接触。1952年底,中国发表了在华日侨情况,表示对于愿意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将予协助,日本可派团前来同中国红十字会协商。1953年1月,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简称“三团体”)首次持日本政府签发的护照来华谈判日侨回国问题,双方商定由日本政府派船接侨,中方负责日侨从住地到乘船前的一切费用,并为他们携带物品、兑换外币提供方便。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前述“三团体”的邀请回访日本时,周总理特别指示李德全团长,将全部日本战犯名单交给日方。之后经过双方的磋商,1062名日本战犯中有1017人于1956年6月至9月分批由日本政府派船接运回国,只有45名罪行严重的,被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这些战犯回国时或再访问中国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还会见过他们,并鼓励他们向前看,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被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为中国的人道主义所感动,每个人都表示要以致力于日中友好的行动,表达将功赎罪之心。时至今日,他们的子女还在继承着父辈的遗志,为日中友好出力。
以上这两件事留下的影响,深深扎根在老一辈日本人民的心里,在一定意义上,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在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民间的往来往往与政府的态度分不开,政府态度好,民间往来就容易些,政府态度不好,民间往来就较困难。
那么为什么在中日关系难以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可以从民间着手呢?这主要是因为,与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政府的态度相反,在日本民间存在着对中国友好、希望与中国交流往来的巨大积极性。日本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顺应历史潮流,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往来,认为这才是日本的出路。所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日本就相继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协会和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等一系列对华友好组织。1953年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决议”。日本社会各界、各阶层,包括社会党、日共等革新政党,以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相继投入到了促进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的行列,甚至在执政的保守党内,也有开明有识之士,主张和支持发展中日关系。
面对这一形势,为了挫败美日政府的反华行径,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航道,周总理审时度势,从现实可能出发,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这实际上成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
开展中日民间关系,无疑首先要从经济方面着手,特别是“贸易先行”,这最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周总理是怎样指导和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1952年4月,周总理指示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正副团长南汉宸和雷任民,邀请三位出席会议的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女)、帆足计和宫腰喜助访华。三位议员不顾日本政府的限制,从莫斯科直接来到中国。中日双方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金额不大意义却非同一般,正是这三位日本朋友的勇敢行动,打开了中日友好的大门。
三位议员访华的消息立即轰动了日本。人民急切地期待从他们那里听到有关新中国的第一手情况。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却以“违反护照法”为名,限制他们组织群众集会并扬言要惩处他们。高良富到外务省门前静坐,要让群众评个谁是谁非,从而挫败了日本政府的阴谋。
莫斯科经济会议后,中日双方先后成立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是这时成立的。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时,周总理让廖承志参加了中国代表团,这不仅出于侨务工作的需要,也是着眼于同日本代表团接触。因为廖承志熟悉日本情况,有不少日本朋友。日本代表团团长是当时鸠山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高达之助,此人在日本侵华时曾任“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周总理同高的会谈正是经过廖承志同志安排的。会谈从日本当时的处境、开展中日贸易的必要性和步骤,一直谈到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和双方面临的困难等等,彼此推心置腹,使高受到很大的触动。60年代初,高连续两次应周总理邀请访华,为打开岸信介内阁造成的中日关系僵局做出了贡献,并同松村谦三一起成为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创始人。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开始后,连续签订了四次民间协议,双方还互办了商品展览会,提出了民间协议、政府支持、官方挂钩的设想。
然而,以民促官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起伏的。
正在两国民间交往蓬勃发展的时候,岸信介于1957年2月上台执政。他一改鸠山、石桥内阁的积极对华政策,进一步亲美反华,甚至声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他无视已谈妥的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拒不批准互设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机构,企图搞“政经分离”,只捞取经济实惠。在后来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中,岸信介政府不仅不严惩暴徒,反称“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构不成刑事案件”,罚款500日元了事。此事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陈毅外长发表谈话,谴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破坏协议。为了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中方宣布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不再延长民间渔业协定,中日贸易一时陷于中断状态,其他方面当然也不能不受影响。
针对岸信介政府阻挠与破坏中日关系发展的恶劣行径,周总理提出了要继续中日贸易和友好关系,日本政府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第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统称政治三原则。同时还提出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指出不讲政治,只讲经济是行不通的;一面对中国抱着露骨的敌意,一面想从中日贸易中捞一把,是肯定办不到的。
中日贸易中断后,一部分靠进口中国的中草药和农副产品维持生计的日本中小企业濒临破产。日本社会党总书记浅沼稻次郎(1960年因主张中日友好被右翼杀害)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事务局长岩井章来华,反映中小企业的困难;曾在万隆会议上见过周总理的高达之助也托人给周总理带信说情。按照政治三原则,本来必须日本政府先改变对华政策,才能恢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从中日友好出发,特别是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实际困难,周总理决定开辟“照顾物资”的途径,绕开双方的外贸单位,两国工会作为联系渠道,继续同中小企业开展贸易,也称“个别照顾”。
1960年8月,周总理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进一步提出了“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周总理向铃木解释说:过去我们想通过民间协议发展贸易关系,但岸信介政府不但不承认民间协议,不保证民间协议的实施,反而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破坏协议。我们不能容忍,只好将中日贸易往来停了两年多,决定今后一切协定必须由两国政府缔结,因为民间协议没有保证。但是没有政府协定不等于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双方可以在企业、公司之间签订民间合同。合同履行得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长期合同。中日贸易中断后,日本中小企业有困难,中国提出了“个别照顾”的办法,叫做“照顾物资”,今后还可以继续下去。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扩大。
周总理相继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既体现了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也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的原则,从而打击了亲美反华势力,支持了对华友好力量,调动了包括部分上层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以民促官,并使中日关系进入了半官半民的备忘录贸易阶段。所谓半官半民,就是民间协议得到政府的同意。
中日贸易中断期间,西欧国家抢占中国市场,中欧贸易迅猛增加。日本经济界担心失去中国市场,要求继岸信介之后上台的池田内阁及早采取行动,改善中日关系。自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如前首相石桥湛山、曾任农林大臣和文部大臣的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以及高达之助等人相继访华,同周总理会谈,探讨打开僵局,发展中日关系的途径。周总理根据日本国内形势变化及时提出,中日不仅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友好,改善关系,还要逐渐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并着重阐述了我国在台湾问题上坚定不移的立场。
松村、高回国后,迫使池田内阁于1962年5月做出了不受美国制约,自主开展对华贸易的决定,同意通过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并默许松村、高负责开展这一工作。1962年10月中日双方签署了长期、综合性贸易文件,称之为《备忘录》,以示同以往民间协议的区别。备忘录的内容是经过两国政府同意的,实际上已接近政府间协定的性质。所以说,从1962年起,中日关系向前跨出半步,进入了半官半民时期。1964年双方互设了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并互派了常驻记者。双方提出以积累渐进方式改善中日关系,即:不仅是贸易关系,也要面向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备忘录贸易会谈中,特别加入了政治会谈,主要是推动日方接受我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逐步排除在这方面的干扰和困难。1971年2月举行备忘录贸易会谈时,中美关系已见解冻迹象,谈判因而比较顺利。日方在会谈公报中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任何形式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都是不能容许的;日蒋“条约”本来就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日方一直借口日蒋条约是1952年以来日本外交依据的基础,不敢碰它。这时首次同意将其列入公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接着公明党访华时,又在上述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恢复日中邦交的五项原则。社会党、民社党、日中议联代表团也相继在同中日友协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支持中方这一原则立场。后来,周总理把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归纳为中日复交三原则。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尚未成熟,但随着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被提了出来,双方进行了探索并为以后的成功解决打好了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经济方面民间往来日益扩大的同时,中日之间在文化、艺术、体育、卫生乃至政界、工会等各个方面的民间往来,或半官半民的往来也日益发展。1955年、1959年两位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和石桥湛山分别访华,主要都是为了探讨发展中日关系问题。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后藤钾二访华。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他访华目的是邀请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双方在商谈会谈纪要的内容上发生激烈争执,我方人员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而且要求把政治三原则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连顺序都不能变,谈判因而陷入僵局。周总理得悉后,立即把有关人员找去开会,批评他们的做法太“左”了。周总理指示,会谈要看对象,看要性质,原则也不能一概照搬,强人所难。后藤先生明确提出“要根据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简称‘国际乒联’)章程,整顿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就是要从国际乒联中把台湾赶出去,恢复我们在国际乒联中的地位,这就是在体育界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由于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及时纠正,才使双方圆满达成协议,我乒乓球队参加了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从而促成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推动了中日、中美建交。这是周总理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又一范例。
据一位专门研究周总理与中日民间外交的学者统计,从1953年7月1日至1972年9月23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周总理共会见日本客人287次,323个代表团次(或批量客人)。在周总理会见的外国客人中,日本客人一直占首位。周总理经常教育我们:“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周总理会见的日本客人中既有各界要人、知名人士,也有满手老茧的普通农民,以及稚气未退的青年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