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禁片导演回归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3月07日 07:46 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
3月,娄烨导演的“个展”将在尤伦斯艺术中心拉开序幕,娄烨电影将首次在影院与内地观众见面。7月,新片《谜》也将在内地公映,这是娄烨阔别内地电影市场9年后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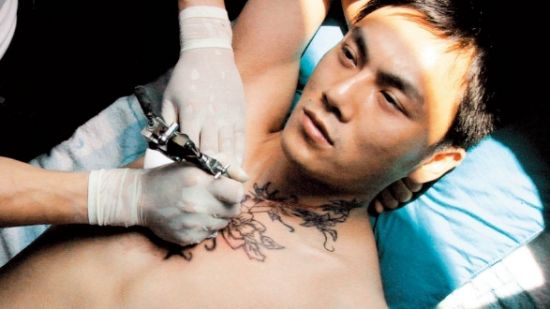 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剧照
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剧照 导演娄烨
导演娄烨5年内,娄烨(微博)有《春风沉醉的夜晚》和《花》两部新片,皆入围三大电影节,其中《春风沉醉的夜晚》还把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这一含金量颇高的奖项收入囊中。此外,从来没有离开过胶片的他,也尝试了用家用DV创作。“豁然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在眼下这个拿个手机都能创作的年代,真的要一个拍电影的人停下来,其实也不那么容易。总的说,这5年对我还算是很扎实的。”
由此就有了“反而禁得自由自在”的说法。娄烨自己不否认:“决定拍就拍了,临时改就改了,所有障碍是创作本身的技术性障碍,创作回归到最本真,充满了乐趣。”但他更强调:“我当然希望自己的电影不会被禁,只有傻瓜才觉得禁得舒服,一个中国导演拍的电影在自己的国家上不了片儿,是遗憾的事,特别遗憾的事。”
娄烨说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都不是原先想好的、设计好的”。最初是学画儿出身,素描,静物,人像,打基础,又一门心思学了三年动画,毕业后顺理成章在美影厂工作。干了两年,却还是想再考中央美院(微博),抱着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何不再报个学校试试的心情,才另又考了个北京电影学院(微博),那年北电动画系不招生,选导演系是出于无奈。
误打误撞成了“85届”的一员。同学是王小帅(微博)、张元(微博)、路学长(微博)、唐大年等人,所谓的“第六代”正由那里源起。“那一届实际是北京电影学院教学改革的一年,整个教学手法变了。后来所谓的‘地下电影’、‘独立电影’,其实真的是和当时学校的改革有关系。那时候我们做作业就是,布置10分钟的短片,但什么都不管,也不给钱,仅提供一点设备。这么四年出了学校,我们发现一切都好办,没钱找钱,没场景谈场景,于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脱离体制的状况。电影学院是‘罪魁祸首’。”
娄烨在学校里拍的第一个短片作业叫《控制》,没有故事,没有情节,作业要当着全班放片并讨论,所以还和老师吵了一架。“老师觉得你得说点什么事儿啊,我说,电影语言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法儿说事儿。”
后来的一个10分钟作业,娄烨又拍了20分钟,还分两部分:一部分纪实方式,拍了在超市里购物付款的全过程;另一部分拍在一个画室里,说一个女人千方百计想把鸡蛋竖在一张椅子上,终于要竖成功时,蛋碎了。“现在看,前部分是《火车进站》,后面就是梅里爱。实际上这是对两种电影可能性的尝试。”娄烨告诉本刊记者。
娄烨喜欢用“褶子”这个词,比如在艺术启蒙问题上,“有一次看西方原作展览,是法国巴比松画派的,已经是离开画室到大自然中,算是他们绘画史的第二次启蒙,而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启蒙。我不是美院学生,对之前的西方绘画史不太清晰,第一接触的是它的第二次启蒙。然后到了电影学院,看得最多的是60年代法国电影、日本电影以及六七十年代新浪潮的电影,也是西方电影的第二次启蒙,而对于我们来说,又是第一次启蒙。这就带来那样的开始,直至今天的作品”。
娄烨走出校门的第一部长片《周末情人》,是和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管虎的《头发乱了》差不多同时诞生的。“混”在一起的电影小子们一起改本子,找办法,甚至干脆相互友情出演,青春的烈度被淋漓挥发,甚至不约而同地让摇滚不仅作为情节结构进入电影,甚至影像表达也不约而同地走起摇滚路线。情绪的碎片,不连贯的事件,晃动漂移的镜头,不安骚动的节奏,故事讲述永远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点为个人细微情绪的表现基础,处处强调了“我”的强烈主观性。
初试牛刀便有国际电影节奖项的认可,至今也被广泛认为的经典作品,娄烨自己却不愿对它过多提及。“开始我觉得是解放的,好像表达是顺畅无比的,但是后来经历了两次剪辑,特别艰难,上影厂的老剪辑师都跟我翻脸了,因为我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因此娄烨便更强调自己此后每一部作品中关于影像的探索,《危情少女》便是回归“作业”式的创作。“我想尝试在一个纪录框架里,可以到达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状况,所以选择了恐怖片的类型。无论人物化妆、色温照度,还是镜头语言,都试图走到极致,就是想看看自己语言的宽度到哪里,呈现的边界在哪里。因为我开始意识到,做电影语言窄毕竟会影响对世界的理解,当摄影机就是我的眼睛时,怎样构成现实就特别直接,语言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接下来的《苏州河》便是迄今接受度最高的娄烨电影,各大国际电影节上捧奖依旧,甚至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年度“十大佳片”之一。影片中,富有物恋癖似的摄影机飘忽不定地扫过废弃的建筑、肮脏的水流、破落的河岸、压抑的廊道、昏暗的酒吧、疲倦的人群,以至观者似乎可以嗅到河水的腐臭味,那并不是我们惯常想象中的上海。
正如罗兰·巴特将城市视为其“现代神话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符号学与都市现象》(SemiologyandtheUrban)中指出,城市最终不过是“一种话语”、“一种语言”,因为现实城市总是人类体验、叙述和评议的存在。《苏州河》里的娄烨用自己的摄影机完成了在一段都市年轻人之间寻求意义又难逃虚无的故事之外,也用极强的主观色彩完成了关于城市的一种叙述构筑。
2003年由刘烨、章子怡、李冰冰(微博)等众多明星主演,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为背景的《紫蝴蝶》,似是娄烨转战商业大银幕的一部作品,但事实上,跳切、重复、闪回、叠化、交叉剪辑仍然频繁出现,娄烨似有意将叙事功能、利于观众情感带入的节点全部一带而过,以大量的停顿、固执的长镜头赋予含混暧昧的信息,加之大量阴雨场景使得冰冷昏暗成为贯穿影片的主调,导致票房惨败至区区数百万元。有关这部电影的影像风格,娄烨如此告诉本刊记者:“我个人认为,最好的画面就是不好的画面,也就是说,最珍贵的影像是非常困难能记录下来的,所以它在技术方面是非常边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一些战地摄影作品,会不知不觉被它吸引,被它感动,但从构图或所谓的美学框架里去衡量这些作品,它都是在边缘的原因。它能直接传达出来一种东西打动你,这就是它的核,是这个文本和那个对象的直接关系,是这个关系打动你,而不是文本本身。实际上,脱离开原型的文本是非常虚空的东西,画是这样,电影也是这样。所以我个人觉得,最边缘、最危险、最困难的记录,可能会得到非常有力量的东西。”
专访娄烨
三联生活周刊:事实上,你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爱情故事,你说过:“我觉得爱情是我们生命之树的一片叶子,在这片叶子上你能够读到整个生活和世界的信息。”这段话我印象极深,但怎么就走到政治的一端?
娄烨:有一点而已吧,政治是背景,它包括主人公的身份等等,是面对现实的创作者逃不开的。你要是在一个荒岛上或者世外桃源让我拍电影,那肯定就没政治了,现在这儿就很难回避。
三联生活周刊:毕竟有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比如好莱坞做法。
娄烨:对。我要在好莱坞也可能很满足于一个爱情故事,但是问题是我在这儿,那就没办法了。我的整个背景都充满了这些信息,你怎么把它排除出去?这可能也是美国导演和内地导演的不同,或者是香港导演和大陆导演的不同。在这方面,我甚至觉得,可能大陆导演和台湾导演还有很多的共同处,但是香港可能区别就会大一些。因此它会引起不同的反响,比如说,这儿就喜欢看好莱坞的作品,可以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嘛,这是好莱坞电影特别好的一面。那个梦想的状况是非常好的,也是这个行业依托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开始适应不了你作品里的激烈,比如很多边缘危险的存在,但实际上,真的接受了故事本身,又觉得好像与自己距离也不遥远,这是你喜欢的角度和切入点么?
娄烨:对。首先是我跟你有一样的感受,才会去拍。你会觉得你身边那些人,你了解得越多,就会觉得原来是这样的生活。然后,其实跟你类似,很多地方都和你自己有类似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说的这个逃不掉的背景,似乎在《春风沉醉的夜晚》里弱化了。那个小城没有地标、没有年代,观众看到的只是相爱的人,他们的感情遭遇,他们的内心起伏,这算是“娄烨电影”某种意义上的转变么?
娄烨:是,有一些。或者说是我更相信人物的本身就带有这个背景了,相信一些人物具体的细节带有社会的反映,这实际上是郁达夫的方式,是郁达夫那一批作者的创作观点吧。我没有创新,只是向他们学习而已,我所说的传统功课就是这个意思。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有一批相信作者是在这个环境里的,便不需要太关注自身之外的太多东西,你本身就是环境的产物,够了。这个做法其实会引起两方面影响,不好的是特别局限在个人,但好的是,同时也有一个自信在那儿——“我”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的存在感是非常强烈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紫蝴蝶》和《春风沉醉的夜晚》都来自你对上世纪30年代文学的迷恋,能具体说说这种迷恋么?
娄烨:一方面我是上海人,很多东西潜移默化。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那时候作品的政治性是弱的,所以它好看。我特别讨厌政治性强的作品,比如说政治性最强的就是样板戏,那样一种政治性介入特别多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它虚假,是为一个理念在工作。这工作就是活好活坏的事儿,就算活很好,观众被感动,我觉得这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如果说那样的电影是一个工具,那你无形中使自己充当了另一个载体:工具,你是在被使用的。因此我比较喜欢一些独立的思考和表达,当然,人必然受到时代周遭的影响,但是他把这些影响放到了作品中,然后有自己的态度,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挺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似乎你的每一部电影都有一定的探索意义,这是《春风沉醉的夜晚》和你之前的作品有一定反差的原因么?
娄烨:这部影片从一开始跟梅峰老师(影片编剧)工作的时候带有一些课题研究性质,即对所谓中国影像气质的找寻。比如什么比较贴近2009、2010年的中国城市状况,其实还是一个电影语言的技术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春风沉醉的夜晚》影像是比较平面的,而且用DV的方式接近被摄对象,没有很多透视、景深处理、构图方式的原因。它更接近于中国画的方式,而不是西方传统影像作品的透视根基,和我之前偏重使用新浪潮手法创作的作品确实反差挺强烈的。
三联生活周刊:距离《紫蝴蝶》时隔近9年,重新面对本土观众,存在适应的问题么?
娄烨:我觉得做小电影就是安全一点,投资也不是特别大,自由度也大,表达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的同时,市场风险也能减弱一点。根本上还是独立电影的做法,成不成真得试试看,肯定会有一些麻烦,但也不能不试试看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现在产业内给“小电影”、“作者电影”的空间是增加了还是减小了?
娄烨:在减小。作者电影的市场空间在减小,更重要的是对作者电影的保护也在减弱。作者电影的作者其实是需要保护的,各个国家都如此,因为所谓作者的风格形成需要时间积累,而作者一旦消逝,需要有作者出现的时候是找不来的。支持作者电影实际是为整体的市场状况做考虑、做铺垫、做准备,这是特别重要的,它可以保持一个市场的丰富性,也会使市场在整体结构上是安全的。单一化、泡沫化的市场结构是不安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产业成熟的必需。
(实习生林磊对本文亦有帮助)
(【新浪尚文-文化艺术】栏目欢迎相关机构合作邀请,详询010-82244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