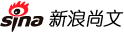朱天文:我不愿被名利场劫持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2日 08:07 mangazine.名牌
“我宁可做一个世俗热闹的人,也不做圣女。”许多年以后,朱天文回顾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不知该是怎样的心情。然而,她此刻的修为却远比当年的期望更高—她没有成为圣女,也没有在世俗的名利场里浮浮沉沉。这又应了她的另一句话:“生命是这样的华丽喜乐,过都过不厌。”
 台湾女作家朱天文
台湾女作家朱天文时隔二十年,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进行她四本文集《传说》、《有所思,乃在大海南》、《炎夏之都》和《世纪末的华丽》的宣传。
朱天文身上有太多的标签:继张爱玲之后最出色的才女作家、侯孝贤的金牌编剧、著名作家胡兰成的徒弟等等……但这些身份却并未将她“劫持”,站在名利场外,她依然勤奋地阅读,刻苦地写作,希望自己可以再写二十年。
 朱天文散文集
朱天文散文集从樱花开启的震撼教育
三十多年前台湾第一次开放观光,朱天文得以走出去,第一站是日本,在她的老师、著名作家胡兰成位于东京的家里住了一个月。
那时的朱天文二十岁出头,日本带给她的震撼,简单说来可以这么概括:“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虽然台湾四季如春,但她是到日本才有机会第一次看到樱花,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她坐在我们面前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记忆依然清晰,面带着看到樱花的欣喜和幸福。
“樱花落的时候是那样飘下去的,”朱天文做了个樱花飘落的手势来描述,“十几里的河边全是樱花,开到最盛的时候,积在地上像下雪,这个风景给你多大的启蒙啊?像我们读的唐诗里,赏花的季节,人们全部出来赏花,那个风景是如此健壮,如此开阔。你到日本,就像我们讲的‘礼失求诸野’,我们中华传统的‘礼’丧失了,就只能到‘野人’日本那里才能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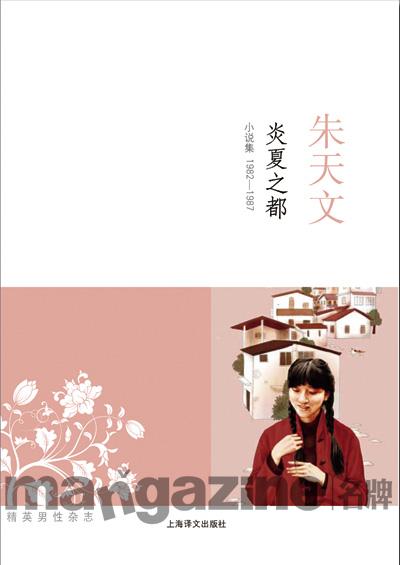 朱天文《炎夏之都》
朱天文《炎夏之都》朱天文把这段去日本的日子比喻成留学,其实也是对传统的再认识。一方面在日本开阔视野,拓展她的人生经历,一方面,老师胡兰成的闭门亲授,让她“接受震撼教育”—胡兰成跟蒋介石同辈,他评价蒋介石,直接就是用骂的。“这不是震撼的教育吗?你从小到大被教育的都是民族救星、民族伟人,一到日本你听到他在大骂蒋介石,太震撼了。”
这一切,让这棵在已在文坛初露头角的小树“爆长十公分”。
 朱天文《传说》
朱天文《传说》先“读万卷书”,后“行万里路”
去日本之前的朱天文常在台北和她的妹妹朱天心还有《三三集刊》的一群朋友读各种书,他们那时是先“读万卷书”,后来“行万里路”。
“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相对论》都看的,当时看不懂但也觉得好看,会觉得那像是看奇幻。”年轻的朱天文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她拿时下大陆年轻人喜欢看穿越、科幻小说做比喻。“继而看爱因斯坦的传记和各行各业人的传记,还有量子力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些东西都喜欢看,这就是为什么阅读使人明智。”
如果给年轻的朱天文写篇“凡客体”,那“爱阅读,爱自由”可以作为开头,她对此的比喻是“人生活在现实的时空,当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就像打开叮猫的一个任意门,立刻就可以不受限于物理的、时间的、空间的限制,也不受限于肉体只能在这个地点的限制,可以到史前时代,到《荷马史诗》的2000年前地中海的现场,这是一个任意门,所以它使人清醒,脱离地心引力,到任何时空中去。”
后来朱天文的旅行选择基本都是古文明国家。去埃及,到土耳其,游历希腊,在地中海沿岸追索古文明的来源。甚至有一次还同父母去尼泊尔和印度参加了一次朝圣团。在开始做编剧后,和导演侯孝贤的十几年合作中,开始接受各种外国电影节邀请,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从“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到罗马、巴黎等地方都跑过了。
“现在就不跑了,”已经年过半百的朱天文说,“现在开始就年轻时走过的地方写些感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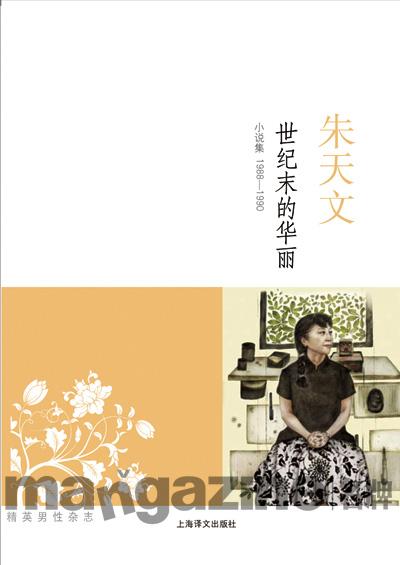 世纪末的华丽
世纪末的华丽阅读,让生活简单而轻盈
朱天文正在创作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是讲“时间差”这个概念的,继二十年前的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这本广受赞誉的小说集出版之后,这是她首次写短篇集,她将环绕时间的差异,个人和世界的时间差,自动化的时间差,经济生活的时间差等各种的时间差来创作。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一直保持创作欲望和保持灵感不枯竭是个奇迹,何况朱天文几乎每两年都有一个电影剧本的创作,朱天文对此的解释是:“每个人年轻时的写作,是凭才华和气场,那是浑然天成写出来的。可是写几年,不再年轻,素材也用完了,还可以用以前累积的老本再持续一阵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东西可以把你引到别的路上去,人生就是无数个小的选择累积成今天的样子,每次小的选择、小的分歧都可能走到另外一条路。像美国诗人福斯特讲的,林间小径分成两条,我选择人迹稀少的一条,风景是另外一种面貌。我总在走一条比较难,比较稀少的,必须去搏斗,搏斗当中其实就会有东西出来。”
而朱天文这么多年在人迹罕至的小径上,搏斗的武器依然是阅读。因为阅读,她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和轻盈。一次主题为“阅读,让我们轻盈”的讲座,主旨就是:生命有限,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活在此时此地,都受限于你的肉身,被物理的条件限制,只有阅读可以让人的身体和生活变得轻盈。
朱天文说
侯孝贤
“在认识侯孝贤以前,我对电影圈的印象并不好,觉得电影圈里没有好人。但侯孝贤和我想象的电影导演不一样,他朴实,也很有才华。他和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默契。无论是写小说,还是电影剧本。这么多年,我写我的文字,他拍他的电影,两个人一起成长,彼此之间给予养分。除了侯孝贤,很难找到频率跟我相同的人。要和其他导演合作,就要先把大家的频率调到一样,彼此没有争执再开始讨论,这是很累的。我时间的沙漏基本上已经倒过来了,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我不会再去尝试和其他人合作。”
胡兰成
“要是胡兰成看到你有什么好处,他不仅当面说,而且四处跟人夸赞这个人怎么样好。我曾经被他这样称赞过,当时不觉得自己有那么好,但听他这么说,真是盛情难却。他夸赞你有这个特质,于是你即便不是这样也要往上蹭,不能辜负他对你的期许。在他的眼光注视下,你会一直往他所期许的方向走。”“小动物把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生物当成自己的妈妈。我对胡兰成的感情就是这样。我在他的启蒙下成长。他把他的智慧、学识直接变成一个果实给我们,我们要做的是,依靠已经到手的果实,从头去把这棵树的根、枝干、树叶画出来。”
张爱玲
“你喜欢一个作家,当然会受其影响,甚至刻意的模仿。我从初中就开始看张爱玲,在我成长期种种的尴尬、不适应,然后我大肆发展自己的这种作怪、任性,后面的支撑就是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随着时间推移,她对我的影响就成了一个我想摆脱的阴影。于是我就采用朱天心的话—‘见佛打佛’,不看张爱玲的书,发现自己和她的不同,慢慢的,从《荒人手记》到《巫言》,我发现我已经摆脱了她的影响。文学本来看的就是差异,个人开个人的花朵,而属于我自己的花朵已经开了。”(文/谭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