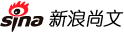长假沙龙:大师云集“理想国”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7日 17:34 精品购物指南
9月底,文坛上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理想国文化沙龙”活动,包括陈丹青、梁文道、易中天、贾樟柯、张大春、舒国治、骆以军、欧阳应霁在内的30人齐聚一堂,他们每一位都堪称大师,这无疑是一场文化盛宴。

创意总监梁文道说:“想象力是逃脱潘多拉匣子的最后馈赠。虽然我们不确切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模样,但至少,不放弃对未来的想象。”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想国”就是被这群书生精心营造出来的“文人共和国”——一个跨越地理界线的社群,一个理性、理念及理想的共同体。作为不甘寂寞的大好青年,参加各种音乐节、电影节、戏剧节,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何不跟随大师,在这个节日为思想插上翅膀,展开一场穿越旷野的想象。
对话陈丹青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乏味到可憎
在“理想国沙龙”里,陈丹青与谢泳对话,他们同样是对民国历史感兴趣,一个偏爱鲁迅,一个偏爱胡适,却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今天我们到底失去了哪些宝贵的东西?谈到“理想国”,陈丹青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正因为不可能才有意思,而对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同样感到忧虑。
“理想国”就是不可能,不可能才有意思
记者:怎么看待这场“理想国沙龙”?
陈丹青:不一定庞大,但蛮丰富,因为请来了这么多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聚到一起大合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部。“理想国”的意思在我来说就是不可能,但就是不可能才有意思,就是不可能我们才会想办法。我期待来的听众不要只是被动地听,要表达自己,我厌恶学校的那种权力关系,永远台上台下,把一切弄得没有意思。
记者:现在沙龙活动很多,这种形式于我们有什么意义?
陈丹青:中国在80年代正式的、非正式的文化沙龙是很多的,大家都很怀念那个时候,这种互动其实不太务实,但是好就好在它务虚,大家谈得天马行空,人文、国家、历史、文艺。但是到了80年代末以来,被人为地强硬中断,大家注意力都转到经济上去了。这些年来媒体又开始操办这些事情,但大多是颁奖活动,带点广告性质,散播点价值观。我想,广西贝贝特要办的“理想国文化沙龙”活动与时下的其他沙龙相比性质不同,它还是想接上十八九世纪那种务虚的、以年轻人为主的活动。
记者:在您的概念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个什么状态?
陈丹青:这2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年轻人的生活乏味到如此可憎的地步,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学生、大学生也不至于如此。我不知道中国的年轻人在就学年龄为什么可以乏味到这个地步,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年轻人最想知道世界、跟年长的人交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他们却没有这样的机会。网络的出现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可怜,年轻人在网络里找朋友,跟虫子在夜里叫一样,好可怜好可怜。
我是一个职业抄袭者
记者:为什么出一个集子专门谈鲁迅?
陈丹青:我是业余写手,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写一个话题,但忽然有人说你写写看,我就会去做。第一次谈大先生,是鲁迅博物馆馆长孙瑜请我去博物馆谈的,不讲鲁迅讲什么呢?可是我有资格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讲了自己感兴趣的,完了之后我完全没想到,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要我陪他各处讲演,这样就有5篇讲演稿,加起来就有6篇,从2005年到2008年,三四年,分散在两本我的杂乱的集子里,现在就出了合集。
记者:有读者说您笔下的鲁迅还原了他的本性,您怎么看?
陈丹青:没有人能够还原哪个历史人物,我只是给出了我自己的想象。我相信台湾和香港的读者也能谈出他们心中真实的鲁迅,而且和我的可能完全不一样。我曾经想过写另外一篇文章,因为两岸隔阂60年,这60年足够出现两岸非常不同的文化,我计划邀请一个现在的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一起谈鲁迅和胡适,最后能谈出三个时间段不同的文化变迁,这中间很难有一个是非。我喜欢胡兰成说鲁迅,他说,鲁迅那时候批评中国就像一个姑娘早上起来梳妆打扮,梳着梳着突然就不高兴,总觉得自己不好看,然后就很不开心。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讲得一本正经批判国民性,其实鲁迅看了会不高兴的,因为一个人在讲一个很大的事情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记者:新书里要用到鲁迅的很多照片?
陈丹青:因为我是画画的,所以总离不开图像,比如我说鲁迅好看,是因为看到他的照片。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八字胡很好看。我部分认知事物是图像告诉我的,文字再呼之欲出都不如图像。古代说有诗为证,我说是有图为证,图像史较文字史早好几万年,动物没有文字语言,但非常清楚危险的靠近。图像对于我来说性命攸关,在所有谈到的人事中,只要有图片我都想要放上,而图像跟文字发生在一起,会很有意思。
记者:说到鲁迅,不得不说最近汪晖抄袭事件,您有关注吗?
陈丹青:我没有看过他的“反抗鲁迅”,几乎他的任何著作我都没看过,基本上所有的学者的著作我都没看过,所以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判断是有还是没有,甚至是对还是错。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是一个职业的抄袭者,我从1989年开始,所有的创作,特别是中年以后最重要的著作,全部是抄袭经典的、古典的绘画图像,抄袭新闻照片,抄袭我能找到的、认为值得的,而且我会告诉大家我在抄袭。这种行为是有道德支持的,这是后现代被确认的方式,叫“挪用占有”。我特别喜欢抄袭,我想了,等我老了没有创造力了,就去临画。我也喜欢用引文写作,就是通篇没有自己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