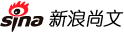陈丹青:圣彼得堡临画记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8日 10:00 南方周末 [ 微博 ]
八十多年过去了。欧洲与俄罗斯各大美术馆的馆员与官员,已经换过好几代人。除了馆内积存的历史档案,恐怕很难找到上世纪负责为中国画家登记临摹的当事人。他们记得那些中国脸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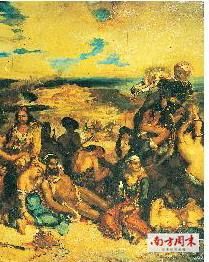 吴作人临摹的德拉克洛瓦《希阿岛屠杀》 1934年
吴作人临摹的德拉克洛瓦《希阿岛屠杀》 1934年
 徐悲鸿临摹的伦勃朗《参孙和大莉拉》 1933年
徐悲鸿临摹的伦勃朗《参孙和大莉拉》 1933年当我每天向苏里科夫馆走去
圣彼得堡,冬宫美术馆。从今年8月初到下旬末,几乎每天,总有二十多位中国油画家散在皇宫南侧小出口的街沿墙角,傍着各自的油画箱,或站或坐,抽烟,聊天,等候大巴士将他们接走。美术馆规定,除了周二休馆日允许全天临摹,其余单日,只能在早晨八点至十点进馆临摹两小时,十点过,观众涌入,临摹者必须离开———美术馆南侧面对涅瓦河,仲夏黄昏,夕阳照亮那一排富丽的宫墙,每到周二,连续画了八小时的中国画家虽然疲倦,仍在留心路过的俄罗斯美人;此外那些天,当画家们上午十点中断临摹,群集候车,日头则高悬空中,真给美术馆南墙投下一片长长的紫蓝色阴影。
申请临摹的手续,繁琐而漫长。事先申报各人选择的经典后,被仔细核对,表格上附印经典画幅的小图像,然后是无数项目的填写。等待批复的过程被翻译细节不断延宕,当馆员在每位画家的画布背后盖上印章,告知翌日可以开始临摹时,大约已耗费了一两个整天———当我在冬宫美术馆办妥临摹手续时,表格的记录显示,仅2010年度登记在册的临摹人数,已有七百多人次。
清晨,大家拎着画具从南侧小门鱼贯而入,经过两道警员关口,查验临时证件,然后进入空无一人的前厅。整座皇宫,刚刚醒来,略有响动就在高高的殿堂发出回声,早已就位的二十多位中年女馆员每人领一位画家走向不同的专馆———自十三到十八世纪的欧洲绘画馆分布二楼,十九到二十世纪的绘画,在三楼———穿过一连串展厅和彼此连接的豪华甬道,两边、四周,布满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普鲁士、法兰西的无数宝藏:成排的镜框与绘画、到处摆放的大小雕像、图案富丽的宫廷挂毯、玻璃柜中数不清的珍玩文物,凝着斑斓而贵重的光泽,停在皇宫窗帘所遮蔽的微明中……转弯,转弯,转弯,二十多位中国画家被巨大宫廷的数百间展室迅速吞没、分散了。各人终于找到自己临摹的那幅画,喘息稍定,于是在大理石或樱桃木地板上小心地摊开画具,开始临摹。女馆员,远远坐在椅子上,静静看守。
所有人的画,收摊后存放二层电梯间。电梯间位于通向伦勃朗专馆一座豪华阶梯的侧廊,里面堆满经年封尘的杂物。我们分别在墙沿靠置各自的画布,翌日取出,再度开始宫殿内的长途跋涉,走向临画的地点———八月中旬末,部分画家转向俄罗斯美术馆临摹十九世纪旧俄经典:同样是每天早晨画两小时,每周二得以工作全天,同样是穿过开馆前空荡荡的大厅,各人消失在列宾或谢洛夫的专馆。当我每天向苏里科夫馆走去,先经过涅斯切洛夫馆,接着是苏里科夫馆偏廊,那里挂着他最后的巨作《斯切潘·拉辛》,然后,我就到了挂着《耶尔玛克征服西伯利亚》和《攻克雪城》的正馆。
这时,在窗外,八点整的阳光灿烂耀眼,美术馆正门外普希金铜像的铜铸卷发,被刚刚照亮。
他们记得那些中国脸吗?
五十多年前,第一批留学苏俄的画家就在圣彼得堡临摹原典。据中央美院留苏前辈李俊老师说,当时,苏联就实行早晨开馆前允许临摹两小时的制度。三十一年前,当我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仓库第一次亲眼看见罗工柳、林冈、李天祥、李俊、张华清、徐明华等留苏学生的临摹作品,无比羡慕,倍感神秘。现在,我们每天经过他们也曾经过的展厅,站在他们凝神观看的经典面前。惟有两项区别:当初他们二十出头,比我如今的岁数年轻一半;此外,这个国家当年叫做苏联。
民国时期,上世纪三十年代,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吴作人等等,也是二十出头,也在欧洲美术馆临摹原典。他们均已故去,没有资料告诉我们,这代人经由怎样的申请进入美术馆,在临摹的日子里,怀抱怎样的激情。
八十多年过去了。欧洲与俄罗斯各大美术馆的馆员与官员,已经换过好几代人。除了馆内积存的历史档案,恐怕很难找到上世纪负责为中国画家登记临摹的当事人。他们记得那些中国脸吗?他们是否知道这些人将自己的临摹带回遥远的中国,从那以后,中国就有了日渐众多的油画家?
马萨其奥与拉斐尔、鲁本斯与伦勃朗、大卫特和安格尔,还有德加、马奈、塞尚、梵高,堂而皇之,挂在墙上,一动不动地永恒着,完全不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老远老远寻到他们跟前,支起画架,摊开画具,一笔一笔仔细临摹他们的画,画中的耶稣或裸女、树林或苹果,被尽可能一模一样地挪到陌生的画布,然后,远去中国。
就我所知,本次展览留洋前辈的临摹作品,过去五十年从未在任何中国的美术馆或美术学院展出过。它们长期封存仓库,可能被记录在早年简陋的纸本档案中,迄今无人问津。历届艺术学生的绝大部分,包括青年教师,从未看过,甚至不知道这些作品。同样,五十多年来,历届史论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包括各代老师教授们,有哪一位曾经发生兴趣,想要观看、整理、研究这些前辈的临摹,或者被允许、被鼓励对这两段历史表示起码的尊敬吗?
临摹,可能向来难以在各种各样的绘画谱系中引起注意,赢得尊敬。所有临摹作品被注定是那唯一经典的无关重要的相似物,有如阴影,既经完成,就被临摹者带走,从此消失了。除了可数的几位临摹者本人就是大师———多产的鲁本斯曾经多次临摹前辈的作品,尤其是提香,在他比较详尽的画册中收入若干临摹,在美术馆,我们会忽然撞见鲁本斯的临摹手迹———无以计数的临摹品,从来不曾,也不可能成为一幅值得记住的画。
一件临摹通常指向声名卓著的美术史经典,但临摹是极端私人的事。我不确知,此番杨飞云同志怎会忽然起念组织团体,来到彼得堡。稍早,他还率领人数较少的一群画家,前往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临摹原典,为期一个月———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留欧留苏两代前辈的临摹行为,可能是在中国移植西方油画不及百年的历程中,绝无仅有的两个时期,与西方经典面对面。自五十年代闭关锁国,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长达三十年间,先是在欧美,后是在苏联,那里的美术馆不再有中国大陆的画家出没其间。始自八十年代,“后‘文革’”第一批中青年画家自费游学欧美,就我所知,中央美院的钟涵先生在布鲁塞尔、浙江美院的蔡亮先生在巴黎,均曾从事临摹,当时他们均已五十岁开外。1986年与1990年,我在大都会美术馆临摹两个夏天,并在馆内遇见上海的魏景山先生,和专事音乐学研究、业余热爱油画的上海人范额伦先生,也在临画。九十年代,范先生甚至如上班似的连续数年天天进馆临画,纯然只为热爱,从未声张。
没有统计告诉我们,过去三十年有多少中国画家自行进入世界著名美术馆,临摹原典。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由杨飞云发起、二十多位中年画家响应的这次活动,是自留欧留苏前辈之后,中国画家第三次集体性出国临摹。
一部中国文人画史,几乎是一部临摹史、戏仿史
我很想知道,欧洲,或者中国,可曾有过专门的研究,定义临摹的性质,考察临摹的动机,清理临摹所能涵括的影响。无可置疑的是,临摹行为几乎与绘画同样古老。上古的绘画不署名,不能传播,没有展览,没有个人或版权意识,更没有风格之说。大量古绘画遗迹显然是对某一无法考证的初本,辗转仿制,有如繁殖,难以辨认作者。先秦两汉的墓室画,古希腊古罗马大壁画,也是某一典范的无数仿制,我们被告知的所谓临摹,即面对某一著名经典的复制性描绘,并被临摹者赋予严肃的文化感,是晚近的事物。
然而面对鲁本斯临摹提香、梵高临摹德拉克洛瓦、毕加索临摹魏拉士开支的作品……我们很难确认临摹的边界,界定什么是临摹,尤其是,为什么临摹———中古时期的拷贝、复制,属于人类初期的传播业;绘画盛期的订件、研习,兼具崇拜与市场的价值;现代与后现代的戏仿、挪移,则是观念与风格的实验。此外,绘画的修复行业、地下的赝品制作,遍及中欧,贯穿美术史。欧美的赝品作坊至今是一大灰色产业,甚至博物馆收藏的两河流域古雕刻,偶然也是伪作。明清之交的江南所谓“苏州样”,曾是高端赝品的专业机构,广罗高手,近年出现在拍卖行的若干古画,虽非名家真迹,时或犹胜一筹。不必说今日中国伪文物制作的猖獗,故宫与敦煌就养着职业的临摹专家,而晋唐宋元的不少旷世名篇,根本就是古人的仿作,并非原典。
这一切,都和临摹行为相类而相通,凡涉及这行为的某一侧重、某一意图、某一功能,我愿贸然称之为广义的临摹。
就临摹行为的忠实度、暧昧感、多样性,甚至制度化,中国书画史充满源远流长的临摹传统。书法之所以成为高雅而永久性的艺术,代代临摹,竞相仿效,是为流传及今的命脉。唐太宗命宫中师傅临写勾填晋代二王的书帖,分赏高官;赵孟頫每天临一遍《兰亭序》,以期维系笔下的雅隽;历代书家的职业日常就是不折不扣的临摹。按照西方的相关定义,一部中国文人画史,几乎是一部临摹史、戏仿史,一部文本与文本不断互动化变的历史。当董其昌公然宣称自己来自博大精深的五代、北宋,或元四家传统,虽其图式或笔路并非如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临摹,但确实各有所本,直指前代的风格与笔墨精义,而清初四王虽则照样声称远接五代北宋的大统,其实是对董其昌那份遗产历历可指的反复模拟。
五四之后的新国画,对应同期进入的西画及其观念,中止了将近七八百年文人画相沿不辍的仿作传统,慕古的风尚逐渐退出水墨实践。近三十年来,由新文人画派勾起的历史记忆与仿古热,与其说是笔墨实验,不如说是戏仿传统的重启与接续,演至今日,大量以明清山水画为仿效资源的当代国画,出现少许有价值有水准的个案,算是顾及水墨画的脸面,使越来越难以辨认文化属性的国画,不至沦亡。
梵高以罕见的天性和能量把经典唱成一首自己的歌
不同文明面对绘画文本的态度,各有不同。欧洲绘画史出现较为主动的临摹画类别———倘若可以称为类别的话———恕我无知,就可见的案例,远在巴洛克时期。其部分形态与中国人略有相似,即为日常的研习之功,但从未将临摹赋予文化的优越感,如中国绘画那样蔚为世代习尚。作为手工艺术而又处于全盛时代,从巴洛克到十九世纪的欧洲临摹品,或是对伟大传统的顶礼致敬,如鲁本斯;或仅仅是订件的需求:有些画家甚至临摹自己的作品,满足市场。我见过库尔贝描绘的四件女性肖像,一模一样,为四位藏家所分属。固然,在风格被稳定传承的时期,个别骄傲的画家临摹经典,意在彰显高贵的来源。洛杉矶一座美术馆藏有德加早年临摹普桑的大画,忠实而精致,不作任何更动,但是奇异地,令人信服地,在每一笔摹写中,十七世纪的普桑风格被微妙转化为十九世纪德加自己的语言。
到了二十世纪,临摹,准确地说,面对一幅经典予以写生式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和表现意图的描绘,出现了。
梵高临摹米勒与德拉克洛瓦的小画,无比富丽,前辈的图式,甚至精神情感,在他手中如火焰般被点燃。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篡改经典,凸显自己,梵高以罕见的天性和能量,在对经典的恳切背诵中,唱成一首自己的歌,经典,也在他手中居然焕发了不可思议的新美感、新语言,俨然是经典自身尚未发掘、尚未实现的部分生命。他甚至在临摹日本浮世绘版画时,倾注了更为忠实的、对异文化的好奇与膜拜,却使这东洋流行小画奇迹般地成为他自己无可替代的标识。
毕加索则以全然自由的、类似行为艺术的姿态,面对经典。巴塞隆纳毕加索博物馆特设巨大的专馆,陈列他晚岁反复模写魏拉士开支《宫娥》一画的大量变体画。在他毕生模写的大量前代经典中,包括中欧北欧若干次要的作品。我们或许不能说那是临摹,但毕加索一生,尤其暮年,阶段性回向整个欧洲造型资源,包括非洲与西亚的艺术,以他所能给出的胆魄与张力,凝视经典,放肆临写,向他自己证明他与伟大传统的联系,就像他郑重其事到卢浮宫看看他的画与西班牙前辈挂在一起,效果究竟怎样。
临摹可以是无限精确的复制,也可以是原典的各种回声;可以是一种绘画行为,也可以是一项文化立场。在中国和其他移植油画的国家,临摹,则是老老实实的学习手段。中国人曾有读书不如背书、背书不如抄书的传统,传统中国文化,对经典与原典无限忠诚,并延续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就此而言,中国人临摹欧洲油画,那原典是新异的,路径却是古老的。
但临摹欧洲原典之于中国油画,尚在初功的阶段,建立并累积这初功,很难,而且很慢。由徐悲鸿一代起始的原典临摹,被中国的历史灾难频频中断。这种灾难的外在形态,大致结束了,但是看看这些前辈们从未展出发表的临摹,多少心血,多少有待深究的问题,五十多年,封尘暗室,从未被善待,甚至未被想起———策展之初,我们曾联系中国美院期以搜寻前辈的临摹,适巧该院仓库渗水,转移藏品,得以窥看逾百件临摹作品,乃仓促提供极其粗糙的照片,最后却不予出借,未能参与本次展览———我们不敢说今次展示的是一批卓越的临摹品,足以适量弥补欧洲原典在中国的严重匮乏,我们更无从知晓,这些临摹品在历代美术教育中,起过或毫无起过的作用。不论中国留洋画家的域外实践多么短暂、寒碜,毕竟两代人曾经诚心诚意临摹了这些画,这是中国油画与西方原典直接沟通的历史档案,仅此一份,无缘亲见欧洲原典的大陆画家,尤其是年轻人,至少,对前辈的临摹应该知道,应该看一看。
固然,那不是原典,而是临摹,八十多年过去了,两代前辈的临摹品如今也成了“原典”:中国人曾经如何在画布上领会大师?我猜,普桑或苏里科夫也会有兴趣瞧一眼。
我画的毕加索!我画的达-芬奇!
8月底,集体临摹结束了。临摹品在俄罗斯的出馆制度比美国稍许松动,并不对画布做事先事后的查验———纽约大都会美术馆限定:所有临摹画布不得与原典同一尺寸。美国人假定,今日仍有神手能够画得以假乱真,偷换原典,带出美术馆———当我们从那电梯间取出各自的临摹,再从木框上剥下来,卷拢了,抱到机场海关,又得履行一项俄国人设置的额外规定:登机运走前,所有油画必须按件付款。
十小时后,壮观的场面出现了:北京机场,三号航站楼,行李大厅,在机场人员的恩准与看护下,我们取出画捆,解开,铺平,摊在就近的地面上:真的,摊在地上,周围人群熙来攘往,每位画家忙着认领自己临摹的画。在一片失去框架支撑而松弛变形的画布上,提香、伦勃朗、沙俄军官、贵妇人,还有雷诺阿的胖裸女,躺满一地,面朝上,全都换了惊恐而好奇的眼神,在这陌生的机场,打量北京。
那一刻,我猜每个人都很开心:功德圆满,画作完好,毕竟,我们各自拎回一件,甚至三四件临摹品,那可是各人勾头耸背、大汗淋漓画出来的———我画的毕加索!我画的达-芬奇!毫无疑问,这是无可渡让的骄傲与虚荣。不过,在俄罗斯,我就看出每个人在临摹完毕后认命地叹气,欲言又止,归于沉默:那也是我的体验。唯有一笔笔临摹,我们这才领教多么难,多么无望。在渐渐呈现的画面中,在越来越多难以把握,无法处理的细节中,抬眼细看、再看、看了又看:原典的每一局部纤毫毕现,同时,完美隐藏着她的所有秘密。
这会是一项奇怪的展览:墙上挂满欧洲大师的熟悉画面,每幅画下的标签是中国人的名字。我说不出此行究竟学到什么,我也无法预见,三代油画家的临摹品会给予观众怎样的启示。多么不合时宜的展示,一切都好像太迟了,又仿佛刚刚发生———远自十七世纪,西洋人给清廷带进欧洲的油画,二十世纪,中国人开始了先去欧洲、后去苏俄的油画之旅。从此,这西来的油画以她无可预料的方式在中国本土蔓延而变异。今天,部分第三代中国油画家远征俄罗斯,在冬宫美术馆与西欧绘画史原典再度交会:说是认祖归宗,说是承接血脉,怕有点夸张、言重、词不达意。我想,本次参与临摹的画家不是为了致用,也不仅为了研究,而是交代一份诚意。这份诚意的郑重与麻烦,只有亲手临摹始得领教,它的过程与历来的临摹行为没有差异,它的意义,惟负载几代人记忆的中国油画家,才能会意罢。(文/陈丹青)